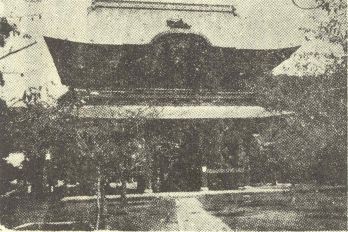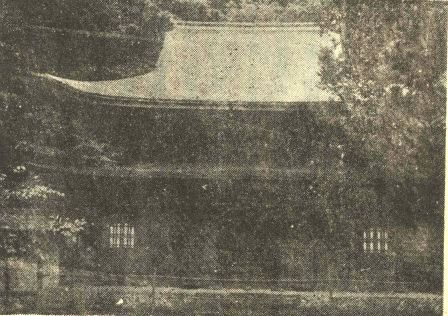入宋日僧,多如遣唐學問僧,當其回國時,多携帶大批佛經,並其他典籍繪畫文物而歸,因之,宋代文化在多方面影響日本文化,今先舉福州版大藏經而言。
福州版大藏經,僅次於太祖開寶年間勅版,乃福州東禪、開元二寺所彫刻。日本現存福州版大藏經,總計有宮內廳圖書寮本,京都醍醐寺、知恩院、東寺、東福寺本等,都為東禪寺版,開元寺版混合藏。古經題跋著者鵜養澈氏,認為兩寺協力完成大藏經(註一)。及至昭和年間高楠順次郎博士主修大正新修大藏經時,經多人研究之結果,始知兩寺各開雕一藏。東禪寺版始於北宋神宗元豐三年(一○八○),福州東福寺住持慧空大師淨真與弟子等,發願雕版。至徽宗崇寧三年(一一○四)完成(註二),費時二十四年。崇寧三年至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又補刊新譯大臺部章疏,共成書六千八百七十卷,是即所謂福州東禪寺版。
福州開元寺版,始於政和二年(一一一五),福州開元寺之慧通大師了一等發願,又刊大藏經,至南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一一四六)完成。經三十餘年,迄孝宗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又補入禪宗部經,亦為六千一百十七卷,即所謂福州開元寺版。兩者都屬私版,東禪寺版,終於崇寧二年(一一○三)奉勅
P.436
名為崇寧萬壽大藏,准稱官藏,因此,並非私版。次於東禪寺版,開元寺版者,則有思溪版和磧砂版。思溪版,亦稱宋版,浙江省湖山之思溪開雕私版。天台宗之淨梵,禪宗之懷深,於湖州思溪(浙江吳興縣)之圓覺禪院,得王永從者之施財,而刻大藏經之版,成書六千卷。其開端始於北宋,而完成於高宗紹興二年者。從來思溪法寶,僅有資福禪寺所刊一藏。但在水原堯榮氏於高野山法藏中,發見思溪圓覺禪院大藏目錄,始判定思溪版有二藏。其一為圓覺禪院所刊,密州觀察使致仕王永從夫婦兄弟等發心捐財鏤板,完成五百五十函,五千四百八十卷,此見於紹興二年(一一三二)題記。其次則為資福禪寺所刊
P.437
,凡五千七百四十卷,完成於嘉興、淳祐之間。磧砂版係湖南省平江磧砂延聖寺所開版(註三)。至於元版。僅於磧砂版補刻幾分,此為元成宗大德年間追雕所誤,此藏完成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這些宋版大藏經,由入宋日僧相繼傳入日本。俊乘坊重源三度入宋,由其携歸宋版經典頗多,依文獻遺品考,則宋版大藏經一藏,或二藏,乃至宋版大般若經一部,或其他宋版經典,於上醍醐類集中建保六年三月文書中,並有記述重源齎歸唐本一切經。
「奚造東大寺上人大和尚重源聊依宿願,從大唐凌蒼海萬里之波浪,渡七千餘軸之經論。」
一切經建久六年(一一九五)十一月七日施入醍醐寺(註四)。這時所建立天竺式經藏,迄今仍存在。以北宋東禪寺版為主,開元寺版補充。又建久八年(一一九七)重源讓狀及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重源於東大寺淨土堂安置唐本及日本一切經。所謂唐本一切經,顯非宋版。宋版大般若經,重源安置於笠置般若台寺,此見於南無阿彌陀佛作善集。淨土堂之唐本一切經,及般若台寺之宋版大般若經,重源僅為安置,是否為其請來,尚無證據,從前後情形推想多分為他請來。其次東寺金剛藏有「奉渡日本重源」墨書及宋版般若心經詒謀抄各一帖(註五)。
宮內廳圖書寮所藏大藏經,以開元寺版為主,以東禪寺版補其不足,但大般若經卷第三十三版刻有「日本國僧慶政捨」,同卷第三十六版心有「日本國僧行一捨板十片」等刊記,妙法蓮華經卷第七版刻有「日本國比丘明仁捨刊換」之刊記。「橋本進吉博士之慶政上人傳考」說:福州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三刻有「日本國僧慶政捨周正刀」刊記云;但行一、明仁之事蹟不明,慶政即山城松尾之勝月房
P.438
慶政。於宋寧宗之嘉定十年(一二一七)曾居泉州,據高山寺舊藏波斯文書端書:
此是南番文字也,南無釋迦如來,南無阿彌陀佛也,兩三人到來舶上望書之(註六)。
爾時大宋嘉定十年丁丑於泉州記之。
為送遣本朝辨和尚。(高辨明惠上人)禪庵令書之,彼和尚殊芳印度之風故也,沙門慶政記之。
由此可知慶政行脚至泉洲,途次訪問東禪、開元二寺,携回大藏經,極為可能。至於行一、明仁二僧或從慶政入宋。或單獨入宋顯無事蹟可憑。但與大藏經之輸入極有關係之僧也。圖書寮本,既有「日本國僧慶政捨」、「日本國僧行一捨板十片」、「日本國比丘捨刊換」等刊記,則元來福州版,無論為東禪寺版,開元寺彼,都經永年歲月始克完成,至慶政入宋時,大藏經已完成百年,因此,就中模板多所缺佚,或磨滅亦不少,當他們印版輸入時,喜捨重雕,以求補足。其他京都戒光寺開山法忍淨業於安貞二年(一二二八),近江菅山寺傳曉上人於建治元年(一二七五),各各舶載宋版大藏經而回。
當時大藏經輸入日本似不止三四部,建曆元年(一二一一)十月十九日,將軍源實朝於鎌倉永福寺,供奉宋版一切經(見吾妻鏡),建長七年(一二五五)十一月九日,前長門寺從位五位上行藤原時朝於常陸鹿島神宮,供養宋本一切經(見遺佚跋語)。前述慶政歸國後,於弘長三年(一二六三),式乾門院利子內親王之十三年忌,所創建京都西山法華山寺(峯堂),舉行唐本一切經供養。此外,奈良市外白毫寺亦有宋片大藏經,弘長二年(一二六二)乃託入宋者輸入,每年三月八日修一切經會,盛況頗大。般若寺及海龍寺,亦有宋版大藏經。般若寺之一切經會,則散見於右經錄,海龍王寺藏經,慶長
P.439
中德川家康移江戶小石川傳通院,明曆之大火燒毀,或散佚,今該院所存,僅有大智論卷第五和大法藏之扁額。
現在京都,奈良及其他諸大寺院等,所宋版大藏經,至少在十藏以上。就中不免有多少遺佚,但這些藏經有東禪寺、開元寺,亦有思溪、磧沙版,這些藏經亦可說為混合版。因未能經逐一精細調查,不敢輕易斷定。據木宮泰彥氏,現存日本大藏經,除一二藏經未十分明瞭,但大都數經過精細調查,茲將日本各大重要寺院所藏之藏經,簡介於次:
一、宮內廳圖書寮藏
以開元寺本為主,其闕本則以東禪寺本補之,本為原清水八幡宮所藏,轉藏宮內廳圖書寮。其中一部為大阪市西區靱上通森佐兵衛氏珍藏,於大正十五年六月獻納宮內廳。(歷史和地理第十八卷第二號藤堂祐範氏「宋版大藏經之零本追記」,「佛典研究」第一號小野玄妙博士「東寺經藏の北宋一切經に就いて」)
二、京都東寺藏
東禪寺本為主,以開元寺本補足。後白河法皇之皇女宣揚門院覲子內親王所藏。仁治三年頃送進東寺。(東寶記第六,「佛典研究」第一號小野玄妙博士「東寺經藏の北宋一切經就いて」)
三、京都知恩院藏
以開元寺本為主,以東禪寺本補充,本為周防山口乘福寺所藏,由毛利家獻於德川家康,慶長中家康
P.440
又送進知恩院。(古經題跋,「佛典研究」第一號小野玄妙博士(同前)
四、京都醍醐寺藏
東禪寺本為主,以開元寺本補足,俊乘坊重源從宋輸入,建久六年十一月七日施入醒醐寺。(醍醐寺座主次第)
五、京都東福寺藏
開元寺本為主,每卷捺三聖寺印。東福寺第五十四世剛中玄柔遺弟子十人赴中國得二藏,永和三年納一藏於東福寺,其他一藏則納日向諸縣郡志布志之大慈寺。(古經題跋,本朝高僧傳卷第三十五玄柔傳)
六、京都南禪寺藏
南禪寺之大藏經,以元版、麗版為主體,以各種版混合,則包括開寶勅版、東禪寺版、開元寺版、思溪版、圓覺禪院版等。
七、奈良唐招提寺藏
思溪版完整,每卷印有唐招提寺印,鹿谷法然院所藏宋版仁王般若經二卷,卷首有唐招提寺印,可知為唐招提所有(古經題跋,寧樂刊經史)。
八、奈良興福寺藏
興福寺宋版大藏經,治承三年九月十八日於該寺金堂舉行唐本一切經供養,依興福寺別當次第記載可
P.441
知。宋藏於治承四年兵火燒失,因此現存宋藏係後傳來,但其傳來關係,文獻未載(寧樂刊經史)。
九、安藝嚴島神社藏
嚴島有輪藏二,一曰龍宮海藏,一曰轉法輪藏,天文中同社大願寺道本上人創建,並有宋版大藏經及高麗版大藏經,古經題跋所記,未見該社,故非現存者。
一○、尾張真福寺藏
本為京都南禪寺塔頭大授庵所藏,應承三十年,原氏女比丘尼玄璋購得,施入真福寺,今散失,僅存湼槃經、大集經、日藏經、月藏經、仁王經、華嚴經等,可謂為東禪寺版、開元寺版混成。
一一、東京增上寺藏
增上寺共有宋版,元版,麗版三藏。宋版為思溪資福寺版,建治元年,近江菅山寺傳曉上人舶齎輸入。每經背捺菅山寺印。慶長十八年奉德川家康命,移入增上寺。
一二、武藏喜多院藏
是思溪版大藏經。
一三、日光輪王寺藏
本為筑前宗像神社所藏,寬永中為黑田長政寄進。(古經題跋)
一四、陸中中尊寺藏
藤原秀衡施入,吾妻鏡載文治五年九月十七日條,見中尊寺一切經。
P.442
此外藏經,諸多散佚,栂尾高山寺有東禪寺版,金澤稱名寺有開元寺版,依古經題跋,稱名寺藏宋版大般若經。這些大藏經如東福寺,由舶載入,非唯鎌倉時代輸入。但宋版大藏經傳入,於此可知其數目不少。大藏經輸入,直接間接刺戟日本開版事業,促進其文化發達,僧行圓於弘安中奉勅著手開版藏經。正安四年(一三○二)版般再讚之刊記云:
去弘安中稱圓上人承勅願之旨,被開一切經之印版,而正安第二之曆林鐘、下旬之天不終大功,遂歸空寂。
P.443
入宋日僧除輸入宋版大藏外,還有佛經論章疏,以及禪籍、儒書、詩文集、醫書等不少輸入日本。
榮西於仁安三年(一一六八)第一次入宋齎歸天臺新論章疏三十部六十卷(註一)。此為天臺座主明雲贈送。泉涌寺之不可棄俊芿當其建曆元年(一二一一)歸國時(註二),携歸典籍,計律宗大小部文三百二十七卷,天臺教觀文字七百一十六卷,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百三卷,法帖御書堂帖等碑文七十六卷,總共二千十三卷。俊芿之弟子聞揚湛海第一次入宋(嘉禎末入宋,寬元二年歸國)携經論疏數千卷(註三)。又東福寺開山圓爾辨圓於仁治二年(一二四一),自宋齎歸典籍達數千卷,這些典籍存於普門院書庫,並作三教典籍目錄(註四)。其法孫虎關師鍊書其傳云:
蓋爾師歸時將來經籍數千卷,見普門院書庫,內外之書充棟焉(註五)。
吾人對俊芿輸入之典籍應特別注意者,其輸入多為儒書:俊芿在臨安時,與錢相公,史丞相、樓參政、楊中郎等儒士往來甚密,不可棄法師傳載: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其書名雖不詳,但當時朱熹集宋學之大成,所著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刊行之時,當俊芿於建曆元年歸國,必携回有朱子宋學四書不少,日人研究宋學,由此逐漸興起。又辨圓携回者,多為佛教經論章疏、僧傳、禪籍、儒書、詩文集、醫書、字書等。辨圓自作三教典籍目錄,惜未傳至今。幸東福寺第二十八世大道一以(辨圓法
P.444
孫),調查普門院藏書之殘書,「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藏於東福寺塔頭常樂寺。此目錄見於木宮泰彥氏著「日本古印刷文化史」中,擇略於次:
經論章疏百七十餘部三百七十餘卷冊,僧傳、禪籍、儒書、詩文集、醫書、字書等二百三十餘部九百六十餘卷冊以上。
這些典籍對於日本文化發展史上,不但為極珍貴的史料,且對於日本五山儒學、文學、詩學影響力極大,辨圓法孫虎關師鍊,就一山一寧質問宋學疑義,認其為日本宋學研究之先驅,他在少壯時代即於京都三聖寺及東福寺,閱覽普門院之藏書。
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目錄當中,有台宗十類因革論四冊、四明十義書科一冊、四明十義書二冊、山家義苑一冊,圓悟錄二冊、佛祖宗流總圖一帖六書,今藏於東福寺。大正七年十一月第四回大藏會所陳列,寺傳為辨圓請來,宋版有普門院藏書印,表紙等也有圓爾墨書。在其目錄所見有魏氏家藏,現為宮內廳圖書寮所藏。該書為宋寶慶三年(一二二七)槧本有普門院藏書印。
俊芿、辨圓等携歸數千卷的典籍,大部分為版本。當時宋代既脫離書寫而進入版本時代,但大批書籍尚未印刻,這於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中,有寫本注書字樣,其他概為版本。此等宋槧本輸入日本,促進日本開版事業發展,在京都,鎌倉盛行唐樣版本。所謂唐樣版,就是以宋、元槧本為覆刻刊版,進而發展有五山版名。又分為博多版、大內版、薩摩版、駿河版等,由此可知,日本中世紀開版事業充分反映出直接受中國文化之影響。
P.445
日本最先模仿唐樣版者,則為京都泉涌寺版,俊芿入宋傳入南山律籍,其弟子聞揚湛海,法孫明觀智鏡、自性道玄等,又相繼入宋學律宗。因此,「深信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杭州為宋代印書的發源地,他們滯留杭州很久,因而曾携大批律部經卷而歸,為謀律宗之再興,就泉涌寺覆刻宋版律部,名泉涌寺版。據大屋德成之寧樂刊經史所述泉涌寺版,共有下列八種刊本。
| 一、 | 佛制比丘六物圖一卷,寬元四年刊,開版者泉涌寺自性道玄。 |
| 二、 | 梵綱經盧舍那佛說心地法門品菩薩戒本一卷,寶治二年刊,開版者聞揚湛海。 |
| 三、 | 資持記及行事鈔一卷,建長四年刊,開版者泉涌寺願行憲靜,助緣者我圓思允。 |
| 四、 |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一帖建長四年刊,開版者泉涌寺願行憲靜,助緣者法華山慶政。 |
| 五、 | 教誡律義一卷,文永十年刊,開版者泉涌寺我圓思允。 |
| 六、 | 盂蘭盆經疏新記一帖,永仁六年刊,開版者泉涌寺叡禪。 |
| 七、 |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一帖,正安元年刊,開版者泉涌寺覺一覺阿。 |
| 八、 | 新刪定四分僧戒本一帖,元亨二年刊開版者泉涌寺會源。 |
泉涌寺版開版之關係者,都為入宋僧或其弟子,開版比丘六物圖者為自性道玄,刊行心地法門品菩薩戒本者為聞揚湛海,都為入宋僧。資持記及行事鈔開版者為願行憲靜(勅諡宗燈律師)乃俊芿之弟子。其助緣者我圓思允,乃俊芿門下之人,法華山寺之慶政為入宋僧,已如前述。他們所開版的,全為宋版之律典。
P.446
次於泉涌寺開版唐樣版者,則為禪宗僧侶,即所謂五山版,禪宗本不以經典為所依,專以參禪究道為宗旨,研究經典或持誦,認為無此必要,因此一般經論章疏開版者甚少,今以開版者多為禪籍。首先開版者,則為禪僧語錄。所謂語錄,乃禪僧平生之語言,例如上堂、小參、普說、拈古、法語,乃至偈頌,佛祖賛、自賛、題拔、書簡等集錄而成。宋之禪寺,常刻經典及語錄,寄贈於人,以為功德。雖遠居海外嗣法門人,亦多寄贈。如仁治三年(一二四三),天童山之如淨禪師語錄,寄贈日本越前永平寺之道元(註六)。嘉元頃宋臨安府徑山之虛舟普渡禪師語錄,寄贈日本洛東草河勝林寺之僧桂堂瓊林(註七),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日本禪宗盛行後,亦多仿傚此種風氣,覆刊宋之碩德語錄,或開版日本語錄,印行禪宗書籍頗多。蓋古人的語句,乃後人參究領會的指南及悟入的機會。
建久二年(一一九一)榮西歸國傳禪以前,日本攝津三寶寺之大日能忍,於參究有所領會,文治五年(一一八九)乃遣其徒練中、勝辨二人入宋贈送書幣於明州育王山之拙庵德光,呈其所悟,求其印證。能忍翻刻,宋明州育王山拙庵德光之潙山大圓禪師警策,是為日本印禪書之嚆矢。當東福寺開山辨圓歸國時,携回數千卷之典籍,置於普門院書庫,自作三教典籍目錄,已如前述,辨圓及其弟子等,當時於普門院興起開版事業。此於普門院現存古文書中,有題「普門院造作並院額等事」,有關該院建造物詳細記載,就中有:
「經藏一宇,圓爾造之,納內外典書籍等。
印版屋一宇,本智房造之」
P.447
於此「經藏一宇」,是收藏辨圓携回數千卷之典籍,所謂普門院書庫,依其細註可以察知。「印版屋一宇」,即為收藏模板之倉庫,即當時之印刷所。本智房諱俊顯,乃辨圓隨從之弟子,即辨圓臨終時,付託東福寺之常樂庵及普門院諸事之僧。日本聖一國師年譜弘安三年五月條:
「二日召俊顯,本智房付常樂庵事云,佛鑑頂相,佛鑑親書宗流及法語法衣直裰卷書等,一一領受勿敢遺墜,但宜勃興叢林能令宗風永遠不斷。二十中日復付俊顯以普門院」。
由此可明白:當時普門院既興造印版屋之建造物,俊顯等遂創立開版事業,殆無疑意。正應元年(一二八八)師元開版應庵和尚語錄、密庵和尚語錄、虎丘和尚語錄,破庵和尚語錄等,翌二年開版雪竇明覺大師語錄,他們不但覆刻宋版,並書辨圓弟子湛海之跋文。
日本禪籍開版,由辨圓弟子俊顯,始於普門院,其次見山庵桂堂瓊林繼之於後。瓊林於文永中入宋(註八),參徑山虛舟普渡,嗣其法而歸,慕入宋僧天祐思順之高風,住草河勝林寺,後構見山庵,韜晦不出世,因此,雖不為世所知,但為開版人天眼目及虛舟和尚語錄之關係者。
人天眼目,乃宋之晦庵智昭所集臨濟、雲門、曹洞,潙仰、法眼等禪宗諸家之要義。日本入宋僧多抄寫而歸,其錯誤頗多,因此,了郜見而慨歎,銳意校正,淨智道人募緣刊行,瓊林書其跋文,其跋文云:
淨智道人希願募藺命工鏤版,以壽其傳,其用心亦可謂勤矣,學者儻思所以扁曰:人天眼目則功不浪施耳,乾元癸卯正月八日桂堂叟瓊林記
P.448
虛舟和尚語錄,即宋之臨安徑山虛舟普度之語錄,前述之人天眼目校正者了郜為幹緣比丘。瓊林開版流布,瓊林親書其序文,蓋瓊林為普度之法嗣。自此時起,日本京都諸禪寺開版事業逐漸發達,虛堂和尚語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等,相繼刊行。虛堂和尚語錄,乃曾住杭州淨慈及徑山虛堂智愚之語錄。日本南浦紹明於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入宋嗣其法,因此,歸國後乃開版先師之語錄,未果即示寂矣。於是其弟子紹崖宗卓(勅諡廣智禪師)繼其志,正和二年(一三一三)於紹明創建之山城龍翔鋟梓,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亦於此時二次開版。一為元應二年(一三二○)由妙秀依宋版覆刻,其鏤版施入京都建仁寺塔頭祥雲庵。一為尼道證於嘉曆四年(一三二九)開版。道證事蹟不詳,乃熱心修禪者,嘉曆三年開版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
以上開版年代極為明確,乃就其遺品所述。但這時開版禪籍非止二三種耳。要依南院國師語錄之乾元元年(一三○二)記事推定,南禪寺之規庵祖圓,依巨山語錄刊行其上堂語錄。巨山諱志源,入宋嗣虛堂智愚法而歸,以宗乘詩偈傳聞叢林間之僧。又同書嘉元二年(一三○四)記事推定,普燈錄之鏤版,喜捨於南禪寺,見其上堂語句。遺存五山版嘉泰普燈錄有二種,同卷末缺刊記,故不明其開版年代,因此可推想為嘉二年所開版。
鎌倉時代,禪宗傳入未久;故未能全脫離舊佛教勢力。例如榮西之所唱禪風,並非純粹的禪,是以復興最澄圓頓禪戒為理想,令法久住鎮護國家為祖師意,最澄將禪列為第三位;榮西以戒為首,以禪為究竟。這如建仁寺,其草創當時即構真言、止觀二院;以行菩薩大戒,亦經臺密,這固非純然禪寺,這
P.449
反映於開版事業,該寺於文永四年(一二六七)開版律典之梵綱菩薩戒本。
綜觀:鎌倉時代所刻版禪籍,及傳文等集,依文獻可考者在三百種以上,此等典籍一方促進五山儒學,詩文學之興隆,一方在日本書籍版式與裝幀上為一大革新。中國書籍凡由禪僧携回之宋版,覆刻印於版式之風,均為唐式,即所謂仿宋本。宋彼有輪廓、界線,日本近世書籍多有輪廓、界線,即受五山版之影響。日本書籍裝幀,初僅有卷子、帖葉、折本等,五山版佛典中雖有折本,其他概與宋版典籍同為綴本。袋綴本僅於紙表印刷,其半折附於表紙以絲綴之,由近世書籍裝幀觀之,可知宋代文化東漸對其影響之大也。
P.450
入宋日僧,不但輸入佛教經典及儒家書籍,並把宋之書畫藝術亦隨同佛典傳入日本。俊乘坊重源入宋三度,其携歸經卷典籍以外的物品頗多。高野山新別院奉安觀音、勢至之唐佛,及唐本十六羅漢像十六舖(註一)。又受法然上人之託,携回淨寺五祖(曇鸞、道綽、善導、懷感、少康)畫像(註二)。淨土五祖像現存日本洛西嵯峨二尊院,其寫生風趣及朱衣金紋之特徵,顯然為南宋畫家之信證。
泉涌寺開山俊芿携歸物品中,據不可棄法師傳載:計有佛舍利三粒,普賢舍利一粒,如庵舍利三粒,釋迦三尊三幅碑文,十六羅漢二本三十二幅,水墨羅漢十八幅,南山靈芝真影一幅等。就中水墨羅漢十八幅(註三),禪月大師(五代人,名貫休,石霜和尚會下掌知客職務)常夢遊西竺,
P.451
親拜生身羅漢,覺後描繪,本為宋室所藏,宋王族出家之比丘尼正大姊(臨安府開化寺),因見俊芿,其貌似第十七慶友尊者,故特贈之,即今京都高臺寺所藏之羅漢像。其貌顎長垂,兩耳過肩,頭凹凸,極為奇特。可謂無遺憾地發揮禪月樣式,這禪月大師之羅漢像與後世之羅漢像影響頗大。又俊芿携歸物品中最珍貴者,則有泰里封國(真里憲即真臘)赤色布一切,多羅華一片(註四)。這是泰里封國獻象於宋朝者,遣三印度僧為使節,他們不通宋語,僅書梵字於乞鉢盂,誰也不解,唯俊芿獨解,給與一鉢,他們大喜,贈此二物也。此外,京都成光寺開山法忍淨業,第二回入宋携歸多種佛像及梵夾(註五)。俊芿弟子聞陽湛海第二回入宋,奉明州白蓮寺(教院五山之一)佛舍利而歸,奉安於泉涌寺,每年九月八日開舍利會定為恒例(註六)。以上就教僧、律僧所述。
禪僧携歸語錄及其禪籍,以及宋之禪師傳授法語、偈頌、肖相贊。這於前述南宋時入宋僧一覽表,可知其大概。他們從宋携歸法語、偈頌,不勝枚舉。禪宗盛於頂相授受之禮,弟子若受其師之印可,往往受其師之頂相(即肖像)以為證。相上又題以贊,或請本人自題,或請其他高僧題之,弟子則揭於禪室之壁間,以為修禪之機緣。
入宋日僧携歸禪宗祖師之頂相贊,大都為宋之畫家所繪授受祖師頂相,或祖師本人自題,或請其他高僧大德題之。即如日本東福寺所藏宋禪師無準師範肖像,此像為該寺開山辨圓入宋師事杭州徑山師範時,請宋地畫工所繪,並請師範題贊,背靠圓椅,手持警策,足以表現頂相畫之規範,其面貌為淡陰影,顯示寫實手法,此為南宋寫實的特色,日本畫家寫實法,多受其影響。入宋僧歸來,携歸這類頂相頗
P.452
多。妙見道祐,覺琳等與辨圓同携回師範頂相贊,山叟惠雲携歸淨慈斷橋妙倫頂相贊,柱堂瓊林携歸徑山虛舟普度頂相贊,這種種描出禪宗興隆的氣象,不獨給日本頂相的形式,以及於寫實手法的影響都很大。
日本雕刻受宋代影響最顯著者,則為宋鑄佛師之參與鑄造東大寺之大佛像,當時重源督造京都東大寺時,曾招致宋人陳和卿等參與鑄佛。據東大寺造立供養記所載,「東大寺之大佛像,乃宋佛師陳和卿與其弟陳佛壽等宋工七人鑄造者,南大山之石獅子及四天王像,亦為宋工字六郞者及其他數人所造」。
日本貞應二年(一二三三)加藤四郞左衞門因其父制陶器之失敗,立志欲完成其父之事業。後堀河天皇貞應二年(一二二三),乃隨永平寺僧道元入宋,學陶器製造法於天目山,在宋五年歸國。經多次失敗,終於發現優良之陶土,試驗成功,遂成有名之瀨戶燒,開日本製陶技術史上之新紀元。彌三右衞隨辨圓入宋,學習織物而歸,在博多創「博多織」,寬喜二年(一二三○)正月最勝光院供養日,日本男女多著唐綾織品,及唐綾小袖等,多仿宋人服飾。日本織物因受宋代的影響,始有長足的進步,這是最顯著的例證。
入宋僧携回物品中,於後世影響最大者,則為榮西於仁安三年(一一六八)第一次入宋即携茶種而歸。茶早於奈良時傳入,專供藥用,及至平安時代,貴族社會及留唐學僧,都有喫茶的嗜好,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六月,始命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植茶,以供每年調口。其後吃茶之風漸盛。日人竟不知茶為何物?唯自榮西携茶種,初植於筑前之背振山,後贈於明惠上人之茶種,亦植於京都栂尾山。栂尾
P.453
明惠上人傳記云:「建仁寺長老(榮西)贈茶,關於醫師,知茶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然此物日本不多,乃尋得其實,植兩三株,誠有醒眠,舒氣之功,亦使眾僧服之或謂此茶子,乃建仁寺僧正禦房(榮西)由大唐携來植育而成者」。在鎌倉及室町時代,栂尾山為日本產茶第一名地,所產之茶,稱為本茶,最為名貴。種茶之風,自是風行全國,講究吃茶之法,始漸風行。建保二年(一二一四年),將軍實朝患病,榮西聞之,特上茶一盞及「所譽茶德之書」,即「喫茶養生記」,稱茶為良藥,甚倡喫茶能養生延齡,又可解悶覺睡;後世所謂茶湯,即「茶禪一味」,是故茶與禪構成密切關係。於是吃茶之風,遂由公卿禪僧之宣導,逐漸推行民間,茶道之開催,茶道之流行,甚至賭茶豪飲以決勝負者,亦漸盛行於日本。因此,日本生活方式,多仿宋式,語言用中國語,服飾飲食,無不以宋為尚,榮西與其徒著宋式大袈裟,大衣,開堂齋時,用宋式饅頭,喫茶,是知宋代文化影響於日本國民生活者,實非鮮矣!
P.454
宋室南遷,跼居臨安,其經濟來源不得不仰賴對外貿易,這時宋船渡日,亦趨頻繁。十二世紀中葉以後,日本平清盛取得政權後,對宋貿易更趨積極態度。據「平家物語」記載,當時平氏府中調度,幾全以「宋物」為中心,其中如楊州的金、荊州的珠、吳郡的綾、蜀江的錦,所有珍寶,無不具備。因為貿易上需要,宋代的銅錢,亦大量流入日本,至今日本各地尚發現此種古幣,即如宋幣以皇宋通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照寧元寶等,其原因在於此。
鎌倉幕府成立以後,不但對宋之貿易更趨積極,即對宋代佛教禪宗尤為重視,由於道元榮西歸國後,積極鼓吹禪宗,因此對宋代所盛行禪宗,更為崇敬,認為唯有奉行禪宗,始可粉碎邪說思想(這指當時親鸞與日蓮所推行佛教制度而言),納亂世人民精神於正規。當時日人對禪宗雖極重視,然對禪宗奧義,究不甚領會,猶待宋代高僧東化,始有光輝騰達的希望!
蒙古人南下,南宋國勢日趨衰危,我國沿海居民多向海外逃避,多數高潔人士,以事無可為,數多遁跡佛門,以為暫時隱逃之計。當時江南佛教呈勃興之象,乃其主要因素。高潔志士衡觀當時局勢發展,唯有東瀛一角,可供暫時逃避異族統治最佳處所,甚至企圖以中日兩國悠久歷史關係,說服幕府,協助宋室恢復中原。迨至回天乏術,整個形勢無法挽回之時;仍以「傳道身份」,留居下來,這是宋代高僧東渡唯一的願望。這與明末遺民朱舜水等渡日之動機,不謀而合。
P.455
宋僧東渡,對於日本文化最具影響力,而見於史籍者,則有道隆等十一人。就中在政治上最具影響者,莫過於蘭溪道隆、兀庵普寧、無學祖元、大休正念等人,至今鎌倉一帶所遺留之禪宗文化,不啻為此等高僧心血的結晶。當蒙古軍侵犯日本時,宋僧又做了鎌倉幕府最高參謀。並於決定和戰之外,且以禪宗精神,鼓勵士氣,使當時實力單薄惶惶不可終日的幕府,兩度撐住了蒙古大軍的襲擊。而忽必列數十萬的海陸軍團,在一夜之間全軍覆滅。這在宋僧,雖然未能達到恢復宋室的宏願,但卻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不僅為日本保全了國土,同時也為宋室報了一箭之仇。這些富有強力民族精神的高僧,在國內固然未能引起史學家重視,即在日本方面,亦復受了德川幕府以後國家主義思想抬頭,對這些有功於日本宋僧的重要史蹟,盡量壓抑而不顯;顯然,這是中日兩國史學家們心理狹窄的結果(註一)。
宋亡,宋僧及學人東渡日本者不少。其可考者為宋了一、普勳、普惠、淨智、吳三郞等。茲將宋僧東渡對日文化最具影響者,分別簡述於次:
蘭溪道隆,宋四川省涪江人,姓冉氏,南宋寧宗嘉定六年生,天性超邁。十三歲入成都大慈寺出家,遊歷諸方,侍講席。後下江入浙,謁無準師範,北磵居簡,日日參究,都無契入,乃杖錫至陽山依無明惠性禪師,一日聞性舉「東
P.456
山牛過窗欞」話,忽焉開悟。寓明州天童山,偶聞日本禪宗漸盛,乃於一二四六(寬元四年),率第子義翁紹仁(普覺禪師)龍江等數人,東渡日本,此為宋代禪僧東渡之始。道隆先與入宋日僧明觀智鏡結交,早有東遊之意。此時日本執權北條時賴。因舊教天臺、真言諸宗,未能脫離舊勢力之覊絆,然為欲獲得宗教上之領導權,乃決意於鎌倉興建大寺院,使鎌倉成為政治及宗教上之中心,而與京都諸寺院對抗。並決意採取中國化之禪宗。當道隆由博多至京都,先訪泉湧寺明觀智鏡老友,因其勸而下鎌倉,初住壽福寺、常樂寺。寶治二年(一二四八),應執權北條時賴邀請,於建長元年在巨福州興建建長寺,是為鎌倉有禪宗道場之始;並請道隆為開山第一代。建長七年(一二五五)二月時賴發願,更號召淋長等一千人應募鑄巨鐘,道隆自作其銘,署名「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註二)。這是日本稱禪寺之始。從來天台、真言與禪宗混淆不清,遂未能獲得全國獨立的地位。而榮西所倡禪宗,屢遭台徒妨碍,遂有宣詔停止達摩宗之活動,然而今道隆在幕府保護之下,依中國叢林清規,鼓吹禪宗。建長寺,為鎌倉五山之一,當道隆開山建長寺時,為大眾所說法語,及所制規則,均富有歷史意義與價值。
P.457
(法語)
「見鞭影而後行即非良馬,待訓辭而發志實非好僧。諸兄弟同住清淨伽藍,已無饑寒之苦,當以此事念茲在茲,若眼光將謝之時其害甚重。所以古人道,饒汝通諸子百家三乘十二分教,於汝分上並不得濟,不若體無漏道,現在當來誠為廣益,旦無漏道作麼生體,每日拖一箇屍體,上上下下喜笑怒駡,更是阿誰,百人中真實,於此回頭返照者鮮,纔有不如意事,使瞋詬而行,如此之者何止一二?參禪辦道只為了此生死大事,豈可沐浴放暇之日,使恣情懶慢。」
(規則)
長老首座,區區力行,不知為誰家事,挂佛袈裟,受信施食,苟無見處,他時戴角披毛,千生萬劫償他去在。今後沐浴之日,昏鐘鳴至二更三點,轉四更至曉鐘時,並要坐禪。不歸堂赴眾者,罰出院,四更五點後,聖僧侍者收洗面桶,五更一點後,若有洗面者,罰油一斤,昏鐘鳴後至定鐘時,不許向火,二更一點後聖僧侍者埋爐中火,若有開向之者,罰二斤油。四更一點至五更二點,並不許向火,犯者罰二斤油,火爐頭,僧堂內並不許說話,犯者罰一斤油,行步有聲,揭簾麤糙者,罰一斤油,堂中所行之事,略呈一二,各宜自守,勿犯此規,謹屯奉聞,餘非文具。
住持蘭溪道隆白。
自此,台徒對他亦無可如何,因而道隆深感時賴盛情云:
「予依大檀那之力,成此大叢林,正如順風使帆」。(註三)道隆經常為幕府內政外交之最高顧問,歷
P.458
經北條長時、政材、時宗諸後,嵯峨上皇聞師道譽,召入宮中問法要,師進一偈曰:「夙緣深厚到扶桑,黍主精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廢仰賢王」。師篤志護,上皇為之感動。師於建仁三年,讓席義翁,歸於鎌倉。幕府詩人,對其崇敬歷久不衰。弘安元年(一二六一)五月示微疾,沐浴更衣書偈曰:「用醫睛術,三十餘年,打翻筋斗,地轉天旋」,置筆辭眾而寂,時年六十六,諡號大覺禪師,是為日本最初對中國僧侶之賜號,名其塔曰:「圓鑒塔」。道隆門下之大覺派,於鎌倉時代以建長寺為,中心,嗣法義翁、葦航、無及、宏辯、約翁等三十四人。並有語錄三卷及拾遺一卷。繼起則為佛光派也,後來東渡之元僧一山一寧,贊道隆曰:「此土禪之初祖」,斯為最正確之贊語。
兀庵普寧,亦蜀人也。幼年出家,遊歷教場,尋出峽,徧參知識,至蔣山(今南京鐘山),值痴絕道沖禪師上堂,大有省悟,轉登育王山(今浙江鄞縣),依無準師範禪師,遂大悟,得印可。端平初,隨無準遷往徑山,無準一日曰:「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之,自然感驗」。師退而兀兀度日,無準乃大書兀庵二字贈之,因以為號。遷靈隱、天童,被推為第一座。尋出象山靈嚴寺,又住常州南禪寺。時日本道俗遙寄書聘請,乃於南宋理宗長定九年(日本文應元年,一二六○)東渡。他與東福寺圓爾辨圓同嗣徑山無準師範法,私交頗深。其東渡前,曾與道隆通書信,道隆亦勸其東渡。普寧由博多上京都,先訪東福寺法弟圓爾辨圓(聖一國師),次應時賴請下鎌倉,弘長元年(一二六○),繼道隆後住持持鎌倉建長寺。時賴因其氣宇非凡,言行超脫,禮遇甚厚。時賴虔誠修學禪定,終至辭卸執權出家,一心參禪。屢依普寧修禪,至弘長二年十月十六日,遂徹悟大事,並獲普寧印可。於是普寧止於建長,大振
P.459
宗風,鎌倉武士與禪宗遂結不解之緣焉。時賴為幕府中心人物,他既熱心參究,並得普寧印可,此對鎌倉武士精神上有莫大之鼓勵與刺激。奠定弘安抗元戰爭的勝利基礎。正當普寧道譽極高之時,雲衲請求掛錫不絕之際,不幸時賴於宏長三年逝世,而眾人又多違觸,遂抱西歸之心,至文永二年(一二六五),一日忽擊鼓上堂告眾曰:
「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
於此可知普寧留偈回國的原因,乃因大檀越時賴圓寂,加之臺密諸多教友嫉妬他的聲望,無端誹謗。普寧不願生於是非之中,故決意歸國。普寧在日僅五年,嗣其法者,僅有東嚴惠安、南州宏深二、三人而已。執權時賴因其開化,達到大徹大悟之境,因而鎌倉武士與禪法更發揮出不可思議的力量。中嚴圓月云:
密(最)以西明寺主平相公,喫兀庵寧公禪師一踏,直下百了千萬,實為我海東禪宗鼎盛權輿也(註四)。
普寧回國,晚住溫州江心寺、龍翔寺。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晏然示寂,壽八十,勅諡宗覺禪師。道隆讓建長寺法席予普寧後,即赴京都住建仁寺。普寧回國後,他又回鎌倉住禪興寺。此寺為時賴所住,在建長寺山內再興最明寺。至文永六年(一二六九),徑山石谿心月之法嗣大休正念(勅諡佛源禪師)東渡。先前時賴曾遣使入宋,請問石谿心月道法,大休正念佛源禪師語錄第三云:
P.460
徑山石谿先師承故大檀那最明寺殿。(時賴)遣使問道,回書中畫一圓相,著語云:「徑山收得江西信云云」:
今檢閱石谿心月禪師語錄,在卷下果有記載下列一偈:
寄日本國相模平將軍
徑山收得江西信,藏在山中五百年,轉送相模賢太平,不煩點破任天然。
但其年代不詳。無象靜照於建長四年入宋嗣石谿心月法,其行狀記有云:
寶祐二年甲寅在佛海師(石谿心月)會裡與佛源禪師(大休正念)聚頭說家裡事,事見千石橋頌軸序,此時平將軍時賢之請簡至矣。
於此可知為宋之寶祐二年即建長六年(一二五四),無象靜照與大休正念同在石谿心月會下之時,亦即時賴請簡到達之時也。建長六年時賴為蘭溪道隆於鎌倉創建長寺之次年,時賴正興隆禪法,自辭卸執權職務,專事參禪辦道之時,因仰慕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第三十六世學德最優之石谿心月道風,特遣使者前往問道,那知石谿心月之法嗣大休正念,就以此因緣而東渡。但其語錄及元亨釋書等都未有此等事記載,未可謂為時賴招請而來也。大休正念(註五)東來,承道隆後住禪興寺,正應二年示寂,歷住建長、壽福、圓覺等諸寺,鼓吹石谿心月宗風,鎌倉武士多所接化,從他語錄中可窺見他的豐富法語,偈頌等。
大休正念以後,至文永八年(一二七一)天童山石帆惟衍之法嗣西澗士曇(勅諡大通禪師)東渡。
P.461
士曇東渡,乃應執權時宗所請,勅諡大通禪師,行實云:
「度宗咸淳六年庚午春月石帆(惟衍)有旨領天童,師(西澗士曇)隨侍行也,七年辛未,有本朝副帥平公時宗釣命,石帆和尚以法語一段勉其行,航海而來,即文永八年也。」
時士曇年僅二十三歲,因此,未住一剎,遊歷京都、鎌倉之間凡七年,弘安元年(一二七八)歸宋,後至正安元年(一二九九)與元僧一山一寧再東渡。住圓覺、建長等(註六)。
弘安元年七月(一二六一),道隆示寂於建長寺,時年六十六。執權時宗為迎請宋代碩德自作下之請帖,遣詮藏主與英典座二僧入宋。
「時宗留意宗乘,積有年序,建營梵苑,安止緇流。但時宗每憶,樹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請宋朝名僧,助行此道,煩詮英二兄,莫憚鯨波險阻,誘引俊傑禪伯,歸來本國,為望而已,不宣
弘安元年十二月廿三日時宗和南
詮藏主禪師
英典座禪師」
詮藏主諱德詮,字曰無及,其事蹟散見於佛源禪師語錄、佛光國師語錄、一山國師語錄、五山記考異、本朝高僧傳,延寶傳燈錄亦有記載。他是蘭溪道隆之弟子建長寺之藏主(藏主專管經藏意),因此名詮藏主。深得時宗信任,後出任鎌倉禪興寺。英典座亦為蘭溪道隆之弟子,諱宗英。建長寺之典座,(掌大眾齋粥);因此名英典座。翌二年五月無學祖元(佛光國師)東渡。祖元與辨圓、普寧同為徑山無
P.462
準師範門下之俊傑,嘗為大傅賈似道所請,曾住臺州真如寺。後因受蒙古侵略威脅,不能安心舉揚宗風,遂至明州天童山,寄居法兄環溪惟一處,擔任第一座主。及時宗請帖到,即動遊心,遂偕法侄鏡堂覺圓,弟子梵光一鏡等東渡。他到鎌倉住建長寺,與壽福寺正念相對峙,大揚禪風。當時執權時宗,及武藏守治宗政為首,鎌倉武士多參禪,弘安四年(一二八一)夏元軍大舉侵襲,迫近日本,為激勵時宗發大勇猛心,堅定抗元。於其語錄可知其壯厲精神。弘安五年十一月於鎌倉建立圓覺寺,請其為開山第一祖。祖元同來鏡堂覺圓(靈圓禪師),乃天童山環溪惟一之法嗣,東渡後歷住禪興、淨智、圓覺、建長、建仁等寺。其次佛光國師語錄載有古澗泉者,其弘長頃東渡。祖元於咸淳(一二六五、一二八四)初在宋開壽寺時,曾遇見剛從日本回國之古澗,談及日本全國上下傾信禪法,尤以執權時賴參禪究道,悟了大事,其臨終儼然為得道高僧,祖
P.463
元聞悉,大為感嘆,並說你再赴日本,我亦同往。古澗亦為東游之宋僧,然其事蹟不為世所知也。
祖元,字子元,號無學。俗姓許氏,明州慶元府人,宋理宗寶慶二年生。七歲就家塾讀書,強記絕倫,年十二,隨父兄遊山寺,聞僧吟「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突潭底水無痕」,默契於懷,已無在俗意。年十三喪父,秋七月,隨師兄赴臨安府,投淨慈寺出家。冬十月禮住持北磵和尚,落髮受具。翌年登徑山,見佛鑑無準師範禪師。十七歲參「狗子無佛性」話,不出僧堂五年,一夜聞首座寮前板聲,忽然發明己事,即作偈曰:
一槌擊碎精靈窟,突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等閒觸著火星飛。
呈無準禪師,準不可之,而示香嚴擊竹頌,師不契。及準示寂,即到靈隱見石谿心月禪師。明年往育王參偃溪聞,再上徑山見石溪,偶聞松源普說,頓忘所得,繼往鷲岸庵參虛堂愚禪師,終有所省。於無準向所示香嚴擊竹頌,及狗子無佛性說,絕無疑惑,時年三十六。德祐元年秋,元兵騷擾,師避難溫州蕩山能仁寺,翌年元兵壓溫州,眾皆逃竄,唯師不去,獨坐堂中,兇暴殘忍之蒙古軍,竟以大刀加於師頸,在大刀逼迫下,他處之泰然
P.464
。口頌「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蒙古大兵聞之,為其氣勢所阻收刀作禮而去。次年,住天童山,訪法兄環溪和尚,環溪留居第一座。時日本建長寺虛席,副元帥北條時宗具書幣,聘師東渡。師將啟行,環溪以無準法衣授之。五月,離太白登船,八月著太宰府,即日本弘安二年秋,下鎌倉入建長寺,開堂說法,北條時宗仰師道化,遂執弟子之禮。
祖元為一烈性之傑僧,他與流寓博多之宋遺民李竹隱,志趣相同。因之,他不僅在精神上為時宗形影相依之偉人,即在抗元戰爭決策上,更為時宗最信賴之偉大導師。弘安四年春(一二八一年),師書「莫煩惱」三字示時宗。時宗不解是何意。師曰:「春夏之交,博多騷擾,不日靜謐,公勿慮」。忽必烈十萬大軍,果於五月侵犯壹岐,在忽必烈絕對優勢遠征軍壓迫之下,情勢日趨危急,而幕府軍力又極薄弱,惶惶不安。時宗迫不得已,血書金剛經與圓覺經,保扶國土,以示抗元的決心。並請祖元為之祈禱,由於祖元誠摯的祈禱,不僅穩定了幕府抗元的意志,鼓勵士氣,而祖元祈禱更發揮出無比的力量。試閱祈禱文句:
「菩薩發大心,不可思議力,剝皮與析骨,書寫佛功德,拔濟苦眾生,皆獲勝好樂,我此日本國,主帥平朝臣,深心學般若,為保億兆民,外魔四來侵,舉國生怖畏,朝臣發勇猛,出血書大經,金剛與圓覺,及於諸般若,精誠所感動,滴血化滄海,滄海渺無際,皆是佛功德。……常說如是經,一句與一偈,一字與一劃,悉化為神兵,猶如天帝釋,與彼修羅戰,念彼般若力,皆獲於勝捷,今此日本國,亦願佛加被,諸聖神武威,彼魔悉降伏,生靈皆得安,皆佛神力故」。
P.465
由於祖元日夜祈禱,更激發時宗斷然行其所信,果然,在一夜之間,竟爾應驗,海上狂風突起,蒙古軍團幾千隻的軍船,悉遭覆沒。未及逃命的元軍,都為日本捕獲成俘,日本稱此為「異國降人」。日本對這批「異國降人」,極為寬待。據元朝「國朝文類庫」載:「此時之所謂新降人,為元軍中之新附軍,即南宋之軍人,日本未殺,便為奴隸。蒙古兵與高麗,則盡處斬云」。因為日人當時只認蒙古人為敵,對舊日宋兵未懷若何怨恨。加之,南宋愛國僧人幕後疏通,以致日方種種寬待。弘安五年,時宗為追慰殲滅元寇陣亡將士,創建圓覺寺,並請祖元禪師開山,當日上野團長樂一翁院豪乞祖元開示法語。祖元隨揮毫書寫香嚴悟道偈法語四幅,迄今日本視為國寶之一。
第一幅:如來正法眼,非今亦非古,父子親不傳,千載密相付,香嚴擊竹偈,幾人錯指注,昨朝問長樂,直答無膡(賸)語,如人白畫行,不用(第二幅)將火炬,又如香象王,擺壞鐵鎖去。摩醯正眼開,
P.466
大撾塗毒鼓,普告大眾去,說偈作證據。公驗甚分明,鵝王自擇乳(第三幅),長樂一翁在,無準老人,雖會中同住,彼彼不相知,四十年後,山野到日本,主巨福山,翁特垂訪,備導前後工夫,辛苦之情,且云,不習語言拙於(第四幅)提唱,乞野人證其是非,野人因舉香嚴悟道偈探之,翁乃作大獅子吼,因陞堂說偈,普示大眾,弘安二年十一月一日,福山山主無學祖元書。
我們對祖元祈禱於一夜之間,殲滅元軍之記載,切不可認為這是天然氣象偶合,要知佛法無邊,這裡寓有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這不獨挽救日本國運,而影響整個亞洲抗元之役,竟出於宋僧在幕後策動與鼓勵,實令人不勝感歎!這些富有濃厚民族精神的宋僧,在國內固然未能引起史學家們重視,在日本亦復受了德川幕府以後,國家主義思想阻碍,使這些有功於日本的宋僧史蹟,遭受壓抑,掩沒而不揚。實為中日史學家們偏差態度所使然。祖元不僅為日本國家的功臣,亦復是中華民族的義士,是中日兩國悠久友好的好榜樣。在此尤應注意者,文永之役後,(一二七五年)元世祖曾數度派遣使節,至日本議和,均因宋僧幕後策動,全部斬決付於鎌倉瀧口,以示堅決。此種措施,實為挑起元世祖一二八一年二次遠征日本主要的因素。此為中日友好邦交史上最珍貴的史蹟,中日兩國史學家們應特別予以表揚!
P.467
茲將宋代東渡之高僧列表於次 ○傳臨濟禪 ※傳曹洞禪 Ⅹ歸宋
| 人名 | 師僧 | 東渡年月 | 在日住所 | 示寂歸國年月 | 根據 |
| ※寂圓 | 孤雲懷奘 | 理宗寶慶三年
(一二二七) | 寶慶、妙法 | | 延寶傳燈錄。 |
| ※義雲 | 寂圓 | 同上 | 寶慶、永平 | 正慶二年十月十二日示寂 | 延寶傳燈錄。 |
| ○蘭溪道隆 | 無明慧性 | 寬祐六年
(一二四六) | 常樂、建長、建仁、禪興、壽福 | 弘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寂 | 大覺禪師語錄,大覺開山塔銘,元亨釋書,聖一國師年譜,本朝高僧傳。 |
| ○義翁紹仁 | 蘭溪道隆 | 同上 | 建長、建仁 | 某年六月二日示寂 | 佛源禪師語錄本朝高僧傳。 |
| ○龍江宣 | 同上 | 同上 | 淨妙 | | 佛源禪師語錄,一山國師語錄。 |
| ○法平 | 同上 | 同上 | | | 大圓禪師語錄。 |
| ○了然法明 | 無準師範 | 淳祐七年
(一二四七) | 出羽玉泉寺 | 文永四年示寂 | 諸宗儀軌,本朝高僧傳。 |
| ○Ⅹ古澗泉 | | 景定元年
(一二六○) | | 文永初歸國 | 佛光國師語錄。 |
P.468
| ○Ⅹ兀庵普寧 | 無準師範 | 景定元年
(一二六○) | 建長 | 文永二年歸國 | 兀菴禪師語錄,東嚴安禪師行實,佛國國師語錄,聖一國師年譜,延寶傳燈錄。 |
| ○大休正念 | 石谿心月 | 咸淳五年
(一二六九) | 建長、壽福、覺圓 | 正應二年十一月寂 | 佛源禪師語錄,法海禪師行狀記,一山國師語錄,元亨釋書,五山記考異。 |
| ○Ⅹ西澗士曇 | 石帆惟衍 | 咸淳七年
(一二七一) | | 弘安元年歸國 | 同上 |
| ○無學祖元 | 無準師範 | 祥興二年
(一二七九) | 建長、圓覺 | 弘安九年九月三日寂
(一二八○) | 佛光國師語錄,無學禪師行狀,佛光禪師塔銘,聖一國師年譜,元亨釋書,延寶傳燈錄。 |
| ○鏡堂覺圓 | 環溪惟一 | 同上 | 禪興、淨智、圓覺、建長、建仁 | 德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寂 | 大圓國師語錄,佛光國師語錄,延寶傳燈錄。 |
| ○梵光一鏡 | 無學祖元 | 同上 | | | 佛光國師語錄。 |
P.469
禪宗傳入日本,雖始於唐代,但以宋代傳入最為特色,以中國禪宗至五代時始大盛。吳越王錢鏐崇奉禪法,改江南各地教寺為禪寺,於是杭州五山十剎,禪寺林立。經北宋、南宋,遂達於極盛時期。當時的佛教,各宗衰落,唯有禪宗,風靡天下,故禪宗為宋代最新鮮的文化。南宋寧宗時代,從衛王史彌遠之奏請,始定江南禪寺之等級,設五山十剎之制,乃倣印度之故事,當時日本僧徒視南宋佛教勝蹟,不啻為西天佛國,仰望之極。
宋代禪宗之東渡,除由入宋日僧輸歸外,宋僧東渡日本主要亦為傳播禪宗。當時宋日交通頻繁,故宋代新文化──禪宗,傳入日本,乃必然之事也。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叡山之僧覺阿與法弟金慶入宋,依臨安景德靈隱禪寺(五山之第二山)佛海慧遠學禪,歸而傳其法。又攝津三寶寺之大日能忍亦自修而有所得,於孝宗淳熙二十六年(一一八九),遣其徒練中、勝辨二人入宋,致書於明州育王山廣利禪寺(五山之第五山)拙庵德光,呈其所悟,而得證明。及至光宗紹熙二年(日本建久二年一一九一),榮西歸日,傳禪宗,遂大盛。這時日本舊宗派如天臺、真言諸宗,經營私利,腐敗衰落,已傷失國民信心,新宗教思想的要求,與時俱進。榮西適於此時回國,鼓吹禪宗,乃適合時代要求,因此大盛。但榮西所傳者,並非純正禪宗,其在京都所建之建仁寺,並構真言、止觀二院,故知其非純正禪寺也。
P.470
由於榮西鼓吹禪宗,喚起時人對禪宗的興趣,自此以後,入宋日僧多以學禪為目的,榮西應為日本禪宗始祖。
武家政治時代,禪宗之所以興盛,其中重要因素有二:主要者為政治上的因素,禪宗為武人所利用,提倡禪宗最力者,則為鎌倉幕府之北條時賴。時賴之皈依禪宗,並非出於誠實的信仰,乃為政治上一種手段。因為武人已取得政權,尚未取得教權。當時日本諸大寺,皆集中於京都一帶,都為皇室公卿所佔據。其所奉行的,則為舊有的天臺宗、真言宗、淨土宗、日蓮宗等。鎌倉幕府視之,自感不滿。於是時賴決於鎌倉建立大寺,使鎌倉不僅為政治中心,並為宗教上之中心,適新興禪宗盛起,對抗舊有宗教,於是引起時賴利用禪宗的動機。
當時日僧道元在越前開永平寺,道元之師明全,為榮西的弟子,道元隨明全入宋求法,明全客死於宋。道元參天童山景德禪寺(五山之第三山)之長翁如淨,傳曹洞宗之正脈而歸。曹洞宗乃禪宗之一支派。時賴遣使赴永平寺(註一),迎道元至鎌倉,自受菩薩大戒,且興土木修大伽藍以供居住,這是時賴提倡禪宗之始。
道元因服膺戒師遺訓。謂「不可親近國王大臣」(註二),在鎌倉僅住半載仍回越前。時賴又迎來日之宋僧蘭溪道隆至鎌倉,開創建長寺,使其為開山第一祖,禪宗自此發達。時賴就學於道隆,又就入日宋僧兀庵普寧參禪;受其印可,竟成一造詣甚深之禪宗門徒。
武家政治時代,禪宗發達第二原因,因禪宗教義,適合武士的精神。禪宗乃中國化之佛教,以寡欲
P.471
質素為宗旨,不重寺院之宏大莊嚴,不為經典文字所拘泥,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也就是不依於文字求解脫,而以苦修力行求頓悟。禪僧除三衣一缽之外,不思居處,不求衣食,奉守百丈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舉凡禪宗之教義,多與時賴幕府所提倡武士精神極吻合,這是禪宗盛行於武家政治時代重要因素。
禪宗以寡慾質素為教,故能克服營私縱慾之念。宋僧無學祖元東渡後,經常對武士說法,他說:「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眾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祖元這種壯烈鼓勵,較諸寡慾質素更進一步,終於「文永」、「弘安」兩役,由於武士服膺祖元的法訓,在一夜之間,竟能粉碎蒙古人陸海軍團的襲擊,全得力於禪宗精神的鼓勵。
北條時賴,初僅為政治上利用禪宗,終因受禪宗薰陶太久,傾向禪宗。一二五六年於建長寺山內再建最明寺(註三)。及至讓政權與北條長時,依道隆出家。福山起願文曰:
「我子孫能奉佛心宗,系胤益昌:蓋家門與禪門為盛衰。」
自此在最明寺,專修禪法,遂成為一虔誠之禪師,及宋僧兀庵普寧東渡,又就其參究,終獲大悟,請其印證(註四),並遣使入宋問道於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之石谿心月,請其法嗣大休正念至日弘法。弘長三年十一月,時賴病於最明寺,臨終著袈裟,端坐繩床,述偈而逝(註五)。儼然為一高僧狀也,宋地盛傳普寧贊時賴像曰:「末後一機超佛越祖」云(見兀庵禪師語錄)。
時賴為幕府中心人物,既得普寧印可,最後一著,又放大異彩。這對鎌倉武士很大的刺戟。例如執
P.472
權時宗,早於道隆,正念參究,又遙遣使者入宋,請求慶元府瑞嚴山開善寺之希叟紹曇之法語,作為修禪的機緣。此事雖未為世所知,但希叟紹曇禪師廣錄中有題「示日本國平將軍法語」一篇,其法語未尾云:
昨承建長鄉老禪師賜書,為閣下需語,三思前輩大老與士大夫,交遊未深,不知造蘊,不敢輕易通信(中略)溫英二兄,奘軸懇言甚切,不獲已,老草奉呈,萬焉目至。
由上文觀之,所謂建長鄉老禪師,即蘭溪道隆、溫英二僧,乃道隆之弟子也。但二僧入宋謁希叟紹曇,為日本平將軍請法語。所謂日本平將軍,為執權時賴?抑為時宗呢?在上文中不詳。一山一寧之圓鑑讚並序云:
圓覺寺比丘宗英,得此鏡於宋國,持歸經三年,後大覺(道隆)返壽福在甲州以鏡送獻云。
當宗英歸國,道隆退隱甲斐,約文永十一年頃,但二僧入宋謁希叟紹曇,當在文永六七年頃,當時時賴歿後已經過七八年矣,因此所謂平將軍者,當指時宗也,時宗曾托二僧索希叟紹曇的法語,於此可知他是如何熱心禪法的人,同時,也是日宋關係史上插一有趣的故事。德溫歸國後,隨從道隆,其與圓鑑關係較深,德雋圓鑑記實云:
「曩焉有比丘宗英者,入宋得鏡,形肖博山,持之而歸後三載,大覺祖師(道隆)遭乎流言,而有甲洲之行,英將其鏡獻之師,以備顧鑑。師旋于相之巨山(巨福山建長寺),未幾逝矣,神足德溫…收師之鏡,本部太守平公時宗追慕師而不可見,晨夜憂想罔怠,一夕夢師告平公曰:死也者人之大常也
P.473
,何故哀之劇,吾之徒德溫有鏡,吾平生愛之也。欲見老僧,看此鏡足矣,覺而召溫索其鏡」。
北條時宗,對於禪宗信仰更深,日人讚時宗為武士之典型,實得力於禪宗。時宗至弘安元年(一一七八)(註六),道隆示寂,這時日本與蒙古人關係極為緊張,時宗自作請帖,遣德詮、宗英二僧入宋,迎請無學祖元。就其實參究道,其事蹟散見於佛光國師語錄,於此可窺見其於禪的修養,近念贊時宗云:法光寺殿(時宗),幼慕西來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註七)。
此外武藏守宗政、左馬權頭貞時、駿河守業時、越前守顯時等北條氏一族,無不學禪。正念、祖元等禪僧,給他們開示法語、偈頌等,不勝枚舉,就中宗政最熱心參究。
正念云:
故檀那武州刺史(宗政)……切切以生死大事為桎梏,孜孜以西來祖意為真歸。無象靜照云:
惟我故武州明公禪門(宗政之法名),慈悲願力,現宰官身,深慕西來直指之宗,早悟即身即佛之旨(註八)。
其末後一著,洒然獨脫,實為當世稀有,北條氏一族以外,武士輩從道隆、正念、祖元參究者甚多,在三僧語錄中,多達五十餘人,而他們多與雲衲相伍,兀兀參究,依禪僧語錄,問答等參究。未領會者,請其開示,例如諏訪入道真性問祖元曰:
昨蒙指誨,要做工夫,奈何公家事忙,做靜工夫不得,望和尚有何方便,令我易入(註九)。
信州四郡左衛門問祖元曰:
P.474
某七八年看狗子無佛性話頭,至今未有分曉(註一○)。
木工左衛門人道圓問祖元曰:
這些武士,逈異於僧侶,各人有職務,為公事奔走,沒有餘暇,往往為一公案費十年二十年歲月,孜孜不倦,念念究道,其精神可佩!
鎌倉武士參禪固多,同時婦女參禪,亦復不少。其在道隆、正念、祖元三語錄中,共有三十餘人。就中時宗夫人覺山志道大師,時宗卒後,依祖元出家。於鎌倉建立道心寺供其住職,終生於此吊念時宗菩提,專事修禪,鏡堂覺圓為覺山志道大師,悟後修業之長文法語,載於鏡堂禪師語錄中,由此可知其修養工夫不淺也。
鎌倉武士多熱心參禪,其精神上所受影響如何?這是最有興趣的問題。要闡明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禪的本質。要依修禪者說:禪,是異於吾心常識,絕對的知識、非有、非空,而有無共存,有無俱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即是禪的本旨。「兩頭俱截斷,一劍倚天寒」,這是禪的境涯。禪,原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不能以言說來說,亦不可以意境來會的絕對真理,是萬古不變。所謂立處皆真,隨處為主。祖元曰:
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眾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註十二)。
P.475
時宗,當國家大難時,斷然貫徹其所信,尤以弘安四年元軍大舉侵犯,迫及博多,仍處之泰然,從容應付,終使元軍覆沒,祖元贊時宗曰:
弘安四年,虜兵百萬在博多,略不經意,但每月請諸老僧與諸僧下語,以法喜禪悅自樂,後果佛天響應,家國貼然,奇哉有此力量,此亦佛法中再來也(註十三)。
時宗於國家危急時,能處之泰然,這全得力於絕對禪定工夫。禪宗對於生死,視之如一,有云:「古來一句,無生無死,萬里雲盡,長江水清」。道元亦云:「生亦時也,死亦時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大休正念更道破生死之念云:
擊碎生死牢關,便見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未心不可得,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方可出生入死,如同遊戲之場,從奪卷舒,常自泰然安靜,胸中不掛寸絲,然立處既真,用處得力」(註十四)。
這種說法,更激發武士出生入死視死如歸的精神。
當元兵大舉攻日,時宗竟能沉著應付,從容以息困難,全得力於修禪的工夫。弘安四年元兵浩蕩進迫博多時,祖元開示時宗曰:「一句一偈,一字一畫,悉化為神兵,如帝釋與阿修羅之戰,我軍得神佛之庇謢,降伏魔軍,生靈皆安」,激發時宗斷然抗元決心,終於一夜粉碎十數萬元軍的攻擊。
時宗死後三周年忌日,祖元說法特贊時宗云:
「人生百歲,七十者稀,法光寺殿(時宗之法號),不滿四十,而功業成就,在七十歲之上。治國平天下,不見喜怒之色,不見矜誇炫耀之氣象,此天下之人傑也。弘安四年虜兵百萬在博多,略不經意
P.476
,但每月請老僧與諸僧下語,以法喜禪悅自樂,後果佛天響應,國家貼然。奇哉有此力量,此示佛法中再來人也。」
於此可知禪宗對武士精神之影響矣!
P.477
在鎌倉最早開版禪籍中,則為兀庵普寧語錄。據其法嗣東嚴惠安行實云:普寧住建長寺時,已開版語錄云。但當文永二年(一二六五)其回國時,在日本已不見其語錄,或已投火燬盡。現行兀庵禪師語錄,乃集在宋時及赴日並歸宋後之法語。亦即住慶元府象山靈嚴廣福禪院語錄,侍者淨韻編,住常州無錫南禪福聖寺語錄,侍者清澤編。東遊語錄,不著標題編者,附載福聖語錄後,住日本巨福山建長寺興國禪寺語錄,侍者道照、景用、禪了編。住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侍者景用編,末附法語雜要。初版不知何時,日本寶永刊本有「小師景用命工鋟刻(小師是弟子意)」,景用為普寧隨從弟子,在普寧語錄中有「示小師景用」題法語一篇。並題「小師景用請賛」。又據其入宋參希叟紹曇,故在希叟紹曇語錄中有題「示日本景用禪人」一偈。殆為普寧於建長寺所開版,說係景用開版。現存語錄,或為依次覆刊而傳至今日者。日本室町時代即已刊行,所謂五山版,為世所重。德川時代之寶永元年,刊無點版,今日已不易得,間有寫本。兀庵為當日東渡諸師最為特色者,其家風亦自異撰,欲窺此硬骨老漢之禪風,蓋非此書(語錄)莫屬,又關於錄鎌倉幕府時賴之史實,亦可於其語錄見之。試舉其印證時賴契悟因緣云:
壬戌十月十六日朝,最明(時賴)啟問:弟子近日坐禪,見得非斷非常底?
師雲:參禪只圖見性,方得千了百當。
P.478
最明曰:和尚方便指示。
師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最明曰:弟子道崇無心。師云:若真箇無心,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指燈云:譬如蠟燭未澆成以前,即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及至澆成點爇輝輝,雅觀照徹明暗,人人瞻望。末後燭盡光極,依舊如前消息。佛出世度人,亦復如是,未出世以前,淨法界身本無出沒,以大悲願力示現,出世成道,隨上中下根機,演說三乘十二分教,拈花示眾,為令聖凡人天大眾,明心見性,末後入無餘湼盤,亦如一條蠟燭,無二無別,萬古流通,直至今日,若見此性,直下便見也。良久云,見麼?
最明曰:森羅萬象,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
師云: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最明言下忽然契悟,通身流汗,乃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望,今一時已滿足,感淚數行,作禮九拜,師即起,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即將自身法衣一頂,付之祝云:公不易到箇田地,宜善護持,令法久住,親付法衣,以表燈燈相聯,續佛慧命,以光末運,萬世愈榮,次為說付法偈:
我無佛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親見燃燈佛。
時賴悟道後,普寧贈之助道頌五首:
老僧初到與三拳,埋恨胸中結此冤,痛慢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妄宣傳。
悟了還向未悟時,著衣喫飯恒順宜。起居動靜曾無別,始信拈花第二機。
P.479
二十一年曾苦辛,尋經討論在精神,驀然模著娘生鼻,翻笑胡僧弄吻唇。
治國治民俱外事,存心存念自工夫,心思路絕略觀看,佛也無法法也無。
壬戌十月十六朝,虛空牶踢不相饒,等閑打破疑團後,大地黃金也會消。
其次,則為宋僧大休正念於壽福寺,開版斷際禪師傳心法要與佛源禪師語錄。傳心法要,乃唐黃檗希運禪師所說,裴休筆錄,以自印心。按黃檗希運禪師,嗣百丈懷海,住洪州高安縣(今江西高安縣)之黃檗山。相國裴休居士官鍾陵(今江西縣進賢縣)時,慕師高德,武宗會昌二年,復請住州之龍興寺,旦夕問法,隨聽隨錄。名曰鍾陵錄。大中二年,居士鎮宛陵(今安徽宣城縣),復請師住其開元寺,旦夕聽道記之,名曰宛陵錄,本書取義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其內容由達摩大師嫡脈相承,提倡以心傳心,不由文字,建立佛心宗之樞要。直截簡明,說示法門要旨,打破生佛、心境、明暗、有無、真妄等相對觀念,主張絕對觀念,故為參禪者一向樂誦,大有裨益於宗門之興隆。
大休正念開版傳心法要自書後敘曰:
「唐好事者刊行此集,流入日本,有檀那越州刺史,篤志內典,公事之暇,喜聞是書,嘗以心要問予,予但勉其制心一處,則無事不辦,因施財命工,以唐本模刊廣傳,欲使本國未信直指之宗者知有,人人此心中,本具一段大光明藏,輝天鑑地,輝古騰今,亦猶毘耶淨名所謂無盡燈也。昔弘安癸未仲春,住金剛壽福禪寺,宋沙門大休正念,書于藏六庵。依此記」。則為弘安六年(一二八三),北條顯時之施財開版。卷末刊記有「端平丙申□□□命工鏤版流通」,端平三年(一二三六)依宋槧本覆
P.480
刊,但當時鎌倉缺乏優秀雕工,頗顯出稚拙的技術。佛源禪師語錄於弘安七年(一二八四)開版,正念圓寂後始印行。如其自述云:
余已首夏,離唐土天童山,是歲孟秋抵日本國關東,遭逢檀度,開法禪興,次遷建長巨福山,再補壽福龜谷山,凡三處住持陞座,小參、普說、法語、讚頌、雜記、侍者輩集而成編,顧予縱心之年,老病侵尋,如太白對殘月,光景倏忽爾,暇日親手刪繁,命工開刊,以待歸寂方可印行(下略)弘安甲申結制日,住壽福寺大休正念序。
至弘安十年(一二八七),相模靈山宴海發願,其徒寶積、寂惠二人開版,傳法正宗記和古倫慧文。建長寺正續庵開版有禪門寶訓集,永仁三年(一二九五)義心開版有禪林僧寶傳,禪門寶訓集如大休正念序云:
諸大老咳唾珠玉珍之曰寶,如世典型遵之曰訓,具眼者輯而成編,垂手後世,照映今昔,為物作則依而行之,可以造聖賢之閫城,箴而佩之,可以去流俗之近習,其於禪林豈小補哉。此書東流,本國識者秘而藏之,禪人慧文命工重刊,以廣其傳,觀其志趣誠可尚也,因說偈以相之,鎮海明珠光照夜,連城白璧本無瑕,叢林千古為龜鑑,言行相應見克家,是為序偈。禪林僧寶傳,如鏡堂覺圓云:
義心禪者募緣將唐本僧寶傳抄寫,重新鋟梓,以廣其傳,書復之覽者,如獲司南之車,可以追配古人之萬一,庶真風不墜也,時永仁乙未孟秋蜀蘇芻鏡堂叟覺圓書。
由此跋文觀之,此等禪籍開版,多為我國東渡高僧所指導也。此外,今日未見其遺品者。執權北條
P.481
時宗弘安中建長寺開山蘭溪道隆之遠忌時,開版圓覺了義經,並命無學祖元普說。佛光國師語錄卷六云:
太守今晨為開山大覺和尚遠忌之辰,雕造如來聖像,雕刻圓覺了義經,命由山野普說云云。
佛光國師語錄,距祖元示寂弘安九年(一二八六)不久時期所開版。建德元年(一三七○)春屋妙葩(勅諡普明國師)於嵯峨之龜山金剛禪院開版,佛光國師語錄卷末刊記有「此錄舊板已漫滅茲者命工重刊」。因此,建德元年以前既經開版,佛光國師塔銘註題云:「元金陵鳳臺古林清茂題佛光國師語錄」。
四明無學祖元禪師(中略),臨終日晏然,說伽陀曰:來亦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毛頭師子吼,此豈事空言,而能顯發光明,如是之盛大者歟?三會語錄門人鏤版印行,携至中國學者爭相傳誦(下略)。
以上所述,是我國東渡高僧促動鎌倉時期,開版事業之發達,已如前述。由於當時日本缺乏優秀雕工,技術拙劣,以致弘安版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之印刷,未十分明顯。因此,日本的禪籍,不得不携至宋地開版,然後携歸鏤版在日本印行。例如建長寺開山蘭溪道隆大覺禪師語錄,其實是他的弟子禪忍、智侃等於宋地開版,禪忍傳不詳,但大覺禪師語錄卷下有題「示禪忍上人」法語,其文云:
老拙(道隆)自主巨福(建長寺)以來,期十三載,荷兄道聚亦已年深,每愛其朴實無偽,屢於談話間,引喻相繫,兄但微笑,而不能盡領。一日炷香出紙云,其欲渡宋瞻覩名山參拜智識,乞一語而為往來受用。
P.482
由此可知二人為道隆隨從之入宋僧也。當其入宋時,携大覺禪師語錄,宋景定三年(弘長二年),請宋臨安府上天竺之佛光法師法照作序文。並請淨慈虛堂智愚依賴校勘,景定五年(文永元年),於紹興府開版,其序文云:
蘭溪隆老出蜀南遊,至蘇臺雙塔,遇無明性禪師室中,舉東山牛過窗欞話,遂有省。於是知松源提破沙盆得所得矣。後十數年,航海之日本,殆若宿契。廼大振宗風,其門下禪忍釋三會語錄請序於余,餘觀其略曰,寒嚴幽谷面面廻春,此土他邦頭頭合轍,故因而序云。時大宋景定三年二月望日,特轉左右衛都僧錄主管教公事住持,上天竺廣大靈感觀音教主,兼住持顯慈集慶教主,傳天臺教觀特賜紫金襴衣,特賜佛光法師法照。
其跋文云:
宋有名衲,自號蘭溪,一筇高出於岷峩,萬里南詢於吳越,陽嶺旨到頭,不識無明,擡腳千胸肯踐,松源家法,乘桴于海,去行日本國中,淵默雷聲,三董半千雄席,積之歲月,遂成簡編。禪忍久侍雪庭,遠訪四明,鋟梓不及處,務要正脈流通,用無盡時,切忌望林止渴,景定甲子春二月虛堂智愚書于淨慈宗鏡堂。
其卷末刊記云:
幹當開版比丘 智侃 祖傳
北京山域州東山建寧寺比丘 禪忍 施財刊行
P.483
天台山萬年報恩光孝禪寺首座比丘 惟俊 點對入板
大宋天台萬年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 妙弘點正施梓
大宋國紹興府南明孫同剡川石嵇刊
據卷末刊記,則知禪忍入宋以前為京都建仁寺(後改為建寧寺)。當刊行時施財印行,時幹當開賴比丘智侃,與禪忍為道隆之弟子。歸國後嗣東福寺圓爾辨圓法,開豐後萬壽寺,即東福寺十世直翁智侃(勅諡佛印禪師),南禪寺椿庭海壽撰東福寺第十世勅諡佛印禪師直翁和尚銘云:
俄有南詢之志,乃禮辭而入宋國焉,偏參諸老乃知法旡異味,歸來再傳蘭溪於建長寺,凡有上堂入室,普說小參等語,篇成錄矣,師再欲入宋國焉,建長(道隆)因付以所編錄,且欲呈平生參見諸老而求印證焉。然而師初謁於大川濟禪師藏校正矣,建平歸來以校正錄呈示蘭溪,溪見不喜矣,師拂袖便出矣,雖然於後刊於世者,即茲本也。
於此可知他所記入宋謁大川濟禪師,請求校正道隆語錄,歸國後開版記。據此,在宋與禪忍僅求虛堂智愚校正,誤傳於宋地開版。總之,因語錄校正,遂觸怒道隆不悅,轉而謁東福寺圓爾辨圓,遂嗣其法。臥雲日件錄,文安五年四月一日條云:
東福寺藏院直宗,本大覺弟子也,將入大唐時,大覺以語錄就癡絕求序,直宗入唐,癡絕已遷化,時虛堂旺化,因請其序,虛堂一見,就語錄中竄滅偈頌,然序而述之,直宗持歸呈大覺,覺大怒,便付一炬,由是直宗嗣東福聖一。
P.484
宮內廳圖書寮所藏「建武元年八月十日云云」有墨書大覺禪師語錄三卷,(京都久原文庫但藏同書下卷),無論其書風或刻風,都優於南宋槧本。其紙質全然與五山版等同為日本紙,由此可知,禪忽、智侃等在宋開版後,携歸鏤版,於日本再為印行也。
於此可知宋代雕工技術影響於日本開版事業頗大。
一個國家的建築物,不僅代表一個國家民族文化水準,也代表一個國家國民經濟力量。宋僧東渡,不唯傳播禪宗文化,並把我國優秀建築學、美術傳入日本;因此,不獨對日本鎌倉武士精神之鼓勵,而對開版事業之發展,亦有顯著的貢獻,已如前述。此外中日兩國僧侶往來,宋代新興文化及工藝技術,不斷移入日本,則在多方面影響於日本文化的建設。
第一、建築方面,宋代輸入日本新文化建築樣式計有二種:一為天竺式,一為唐式。天竺樣式,當源賴朝,再建東大寺佛殿,即由俊芿坊重源移入天竺樣式,並由其監督工事,此為眾所知之事。重源最初入宋,本欲巡禮五臺山聖蹟,未達其目的,即回歸日本。後第二次入宋(註一)。實為準備再建東大佛殿,故於宋地研究建築樣式,在此時間運送國防材料,建立明州育王山舍利殿,就大建築物上獲得實際經驗。關於大佛殿再建工人等,後來分散全國,傳授其建築技術,因宋式建築不合日人的風味,現在遺存宋式建築物中,僅有東大寺南大門,山城醍醐寺之經藏,播摩淨土寺之淨土堂,是為最顯著的例子。
P.485
按東大寺,乃聖武天皇為求國泰民安,興建此寺。於天平十七年(七四五)開始鑄造銅大佛,至天平勝寶元年(七四九)完工,勝寶四年四月開光。大佛殿不幸於治承四年(一一八○)遭燬。俊乘坊重源再建(建久六年),永祿十年(一五六七)又遭戰火燬壞。現今佛殿,乃元祿五年(一六九二)再建,目前僅有南大門係俊乘坊所建也。
唐式,亦稱禪宗樣式,乃日本禪僧傳入宋代禪剎之樣式,榮西殆為傳入之始祖。這給日本建築上甚大之影響。榮西在宋中(註二),天台山萬年寺三門兩廊之營造,及智者大師塔院之修建,以及協助天童山千佛閣等建築工程,頗獲有多種建築工程之經驗,於是他歸國後,竭力鼓吹禪宗。並於博多建立聖福寺(建久六年建立),鎌倉建立壽福寺(正治二年建立)。京都建立建仁寺(建仁二年建立),多模仿宋代叢林清規及宋代禪剎樣式建立。次為入宋之道元歸國後,則於天福元年(一二三三),於山城建立興聖寺,該寺僧堂全採宋代風格。
京都東福寺開山圓爾辨圓(聖一國師),他於善禎元年(一二三五)入宋。仁治二年(一二四一)歸國。在宋六年,都在徑山,師事無準師範,當時徑山於紹定六年四月遭受火災,全山燒燬殆盡(註三)。師範慘淡經營,建立幾多大伽藍,因此,辨圓目覩大規模建築樣式,獲得豐富的經驗。當其回國後,即於京都建立東福寺,多仿照徑山樣式。雖說這時日本禪宗,並非純粹的禪宗,乃有天台、真言兩宗混淆其中,這時寺院的建築,亦多非純粹禪剎的建築,天台、真言的建築互相交雜其中,例如建仁寺,即有真言、止觀二院的建立,東福寺亦有天台、真言建築的滋味,光明峯寺入道前,則有顯明的分別:
P.486
東西廻廊各二十六間,合五十二間瓦葺
東西壁奉圖繪,西天廿八祖,震旦六祖,並真言八祖,天台六祖等行狀。(中略)
灌頂堂一宇、五間四面南面禮堂,號莊嚴藏院
奉安置兩界曼荼羅各一舖,
八祖師像各一舖(中略)
寶藏二宇、三間二面瓦葺
一宇密宗章疏並寶物等
一宇顯宗章疏並俗書等(下略)
於此可知當時皆為天台、真言混合建築之禪院,然而,純粹禪宗建築寺院在何處?殆為建長五年(一二五三)完竣之鎌倉建長寺。建長寺草建人佛記古寫本,所記當時該寺創建的規模:
法堂十七間,四面高三丈二重二丈五尺,本房方丈十間八間半
客殿十三間、九間半,庫房八間五間半
經堂五重八間四間高六丈二尺,山門高二丈、平五間橫三間半
中門高二丈五尺、平七間橫四間半 禪堂十間七間
鐘樓五間四間 修樓八間四面
食樓五間四間
P.487
由此觀之,建長寺創立的當時,大體上完備了禪宗建築的規模。北條時賴特別迎聘來自宋朝禪師蘭溪道隆,為其建立此寺,並請道隆為開山。建長七年(一二五五)該寺又鑄造巨鐘,開山道隆自作鐘銘,署名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可謂名實相符完備禪寺,故禪剎之建築可謂始於建長寺。自此以後,因禪宗發達,禪興寺(註四)、壽福寺、圓覺寺(註五)、淨智寺(註六),相次建立。凡興建禪剎,多與宋僧道隆、正念、祖元等商討,無不倣照宋代禪剎樣式,金澤大乘寺傳說為五山十剎圖,該寺開山為徹通義介,他於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入宋,遍曆五山十剎,親自描繪,對其建築樣式及堂內設備,都與描繪圖樣相似,該寺藏有其所繪之圖樣。京都東福寺及若狹常高寺,多有入宋僧携歸的圖樣。當時禪僧往來,諸如此類圖樣携歸者頗多。此種圖樣應用於日本禪寺之建築及堂內設備,不但為寺院建築的標準藍圖,即日本一般住室之所謂書院造、玄關,亦多由禪寺廻廊等銳化而成者。新編相模風土記云:建立圓覺寺時,曾遣日本工匠入宋,調查徑山諸堂設備,並倣照其規模建立,當時中日交通頻繁,前往調查極為可能的事。並招聘宋代工匠至日本領導。佛源禪師(大休正念)語錄中則有宋人朗元房、行恭、宗德等名,朗元房見於佛光國師語錄,為時宗侍醫。但其他二人事蹟不明。總之,當時鎌倉除
P.488
僧侶以外之宋人留在,多為建立禪寺之工匠。
第二、美術工藝方面,東大寺大佛修鑄時,宋代鑄佛師對於日本鑄物技術貢獻頗大。初計畫修鑄大佛(註七),義和元年(一一八一)三月造佛長官藤原行隆,率領鑄佛師十餘人檢討,如何進行工作,諸多鑄師一致說:「此事非人力之所及,我輩既蒙勅召,當盡微力」,卻躊躇不前。恰巧次年壽永元年,宋代鑄師陳和卿等乘商舶東來,遂招陳和卿計議鑄佛的事,因得陳氏主鑄工程,故大佛之鑄成,全為陳氏之功德(請參閱本章第三節)。
加藤四郎左衛門景正者(註八),隨道元入宋,他在宋朝研究陶器術製造歸國後,則於尾張瀨戶開窯,所謂「瀨戶燒」,使日本制陶器術劃一新紀元。彌三隨辨圓入宋,傳習廣東織,緞子織歸國,則於博多創博多織,名氣甚高(請參閱第三節),其他不勝枚舉。
第三、醫學方面,榮西得宋醫口傳,歸國後著「喫茶養生記」,說明喫茶有益於人生,卻病醒神,養生延齡。榮西自書中謂:
同書終云:
此等記錄皆有稟承大國乎,若不審之輩到大國詢問無隱歟?
但榮西在宋朝,就宋醫學醫方之事蹟不明,入宋僧諸如此類者甚多。例如隨道元入宋之木下正道(俗名藤原隆英),學得解毒九制法而歸,即其一例。又如前述宋醫朗元房,在鎌倉三十餘年,深得時
P.489
賴、時宗之信任,尊為侍醫,因此,對日醫學發達不少貢獻。
其他,無論入宋日僧,或東渡宋僧,其所傳佛教,無論內容或外形,全為中國化的禪宗。因此,其日常生活中,多帶有宋代風味。這於日本人日常生活方式,亦有很多的影響。例如他們宣揚禪宗,多以中國語文發表他們的見解,或以中國語文等表揚自己的見地,這於他們語錄中不難窺知其內容,此對日本語文,漢文學亦有很大的影響力。入宋日僧歸國,不僅携回大批禪籍語錄,並把宋代第一流禪僧墨跡携至日本,若圜悟克勒、大慧宗杲、密庵咸傑、無準師範、古林清茂、了庵清欲、馮子振、趙子昻等墨跡携回日本,現均為日本國寶。日人酷愛中國文化,於此可見矣。
榮西和他的弟子都著宋代大袈裟、大衣,其他一般衣服,或調味品而論,亦多帶有宋代的風味。當時食物調理法,盛行宋風,即為顯著例證。圓覺寺開堂齋供常食饅頭,此僅為一例,其他例子不勝枚舉。宋風起初始於禪剎寺院,後來歸依禪剎的上流社會人物漸多,於是宋風又逐漸推行於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