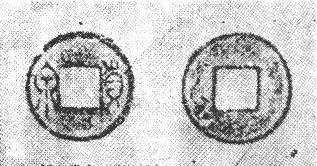P.21
日本為西太平洋中的島國,孤懸於海洋中,橫於亞洲大陸門前,環境特殊,開國以來,自有一脈相貫的歷史。其與我國僅隔一衣帶水,其種族文化,政經典章之關係,最為密切,尤以佛教關係為最。二千年來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佛教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重要地位。中國人不可不知日本歷史,猶如日本人不可不知中國歷史,更不可不知佛教於中日關係史上之重要性。因之,吾人要研究中日佛教交通史,更不可不追溯先史以前兩國文化悠久之關係,以探求兩國先民往來的蹤跡。
據地質學者之考證:遠在冲積世以前,日本並非像目前的海洋群島國家,其西南方以陸橋的形式,而與我國大陸相連接。在此時期,人類的移動往來,乃屬必然的事件!
在地質學上,冲積世之初,冲積世之末,日本群島在地質上發生極大的變化,經三番五次地殼分裂與溶解,遂使日本與大陸往來的陸橋,全部陷入海底,結果使其成為純粹海島,隨即開始所謂「繩紋式文化」,以新石器為中心。因此,在日本始終未發現舊石器時代的石製器品,這一個新石器時代突然產生,正說明了必有一個經舊石器文化培養民族洪流,進入日本群島。今日日本人自稱其民族為大和民族——又稱天孫民族、或天降民族,謂大和民族之祖先,並非自有日本列島以來,即棲居於該島,而是
P.22
由其他各地移住日本者。此已為今日一般人類學者所公認(註一)。在原始時代,由外地移往日本列島之各民族(註二),大體均利用海流為其渡日之自然航路。
舊石器時代(約距今二十萬年至一萬年以前)之遺跡,日本迄今尚未發見。美國動物考古學家摩斯(Muse)任東京大學教席,於明治十一年(西紀一八七八年),發掘東京大森之貝塜,始斷定日本有新石器時代之遺跡(註三)。當時摩斯認為從貝塜所遺留日本石器時代人的遺跡看來,這個原始石器時代的人實為蝦夷民族以前的先住民族。但在此以前,西洋學者中,多認蝦夷民族為日本島最初土著。於是兩者之間,頗有爭論,在主張蝦夷說日本學者之中,亦不一致。著名的西鮑德(Sabald)父子,及小金井良精、白井光太郎、鳥居龍藏等諸人,尤以小金井博士於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就所集蝦夷骨骼與東京帝大所藏的若干貝塜所發掘人骨作比較研究,兩者之間,並無不同之處,於是認定日本石器時代的居民,即為蝦夷。
據原始的傳說:蝦夷原住於日本群島,不久為外來的民族所壓迫,逐漸北上,終於到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
一般史學者咸認在外來民族進入群島以前,蝦夷民族為固有的土著,應無問題。但所成問題者,即為驅逐此蝦夷民族北上,發展所謂大和民族的日本民族,究為何種民族?其發源地又在何處?早在一九四八年,日本民族學協會以「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與日本國家的形成」為題——民族學研究第十三卷第三號——邀請岡正雄、江上波夫、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等多位學者,舉行座談會。在座談會中
P.23
,各人見解殊不一致,但對江上波夫所主張所謂「騎馬民族說」,卻認為日本國家的起源,係奠基於北方騎馬民族的侵入統一之見解。另有認為日本民族的基層文化中很多應該在華南民族諸文化追求其起源之主張,而有識之士頗有一種新趨向,即欲將日本民族的起源與華南或東南亞洲連結一起,加以討論。這種動向逐漸成熟,於是日本民族學協會乃於一九五八年以「第一次東南亞洲稻作民族文化綜合研究」為題,進行湄公河流域的民族學調查(註四)。江上波夫認為日本民族在「無土器文化」與「古墳文化」之過程中,經常因北方大陸,華東、華南各地人種渡來的結果,形成了一種極為顯著的混血民族,但其中以皇室為中心的支配層,則由我國東北經由朝鮮半島,於四至五世紀之間,進入日本的「騎馬民族」。此等具有高度文化的騎馬民族,在部落國家分立的原始社會中,不旋踵就成了社會的中樞,建立強而有力的政權(註五)。江上波夫的主張,雖仍在討論之中,但無論從何種觀點研究,大陸民族對日本民族血統的影響,以及在大和地區建立全國中樞,逐漸統一部落國家民族的主張,已為多數史學家所公認,成為定論。栗山周一氏亦云:「日本人並非日本列島之特產者,亦非自高天原飛來者,而是早在原始時代,於不知何時從彼大陸向東海之花彩列島渡涉而來的,故在科學上而言,高天原應求諸大陸。至於主張日本史與其他民族毫無任何關係之說,乃一種錯誤之見解。……日本文化係以大陸文化為根幹,故其根源在於大陸。……而中國大陸之漢民族,早在日本列島完成統一成立國家以前,便已具有冠於世界之文化,而漢民族文化逐漸自朝鮮半島進入日本。」(註六)誠如周一氏云:日本古代的文化,是以大陸漢民族文化為根幹。
P.24
東京大學長谷部博士亦主張華南地區為日本石器時代人的故鄉,於是認定日本民族與華南地區先民有其不解的因緣。在地質學上洪積世(最新世)的末期,琉球列島以西的一部分,尚有淺灘可與我大陸相連接,故日本石器時代居民,即由大陸循此淺灘進入日本群島。在此時期(洪積世末期),朝鮮海峽以及津輕海峽,業已形成。故北方民族渡來之說,甚少可能,雖有循琉球列島淺灘通過,故由華南渡來的機會,較為自然而且多。
近世日本地質學者證明,去今五、六千年以前,東南沿海與日本九州一帶,其海水僅深可入腹,一般先民盡可自由往來,這不啻給長谷部博士主張一有力的印證。京都大學人類學者清野謙次博士,主張係由於有史以前大陸系人種之經由朝鮮半島,大規模進入群島,而與當時石器時代之日本原住居民,互相混血之結果。九州大學教授金關丈夫博士承繼清野博士主張,徵諸史實,加以考察、研究,證實大陸大規模的移民,在大和時代進入三島,其「歸化」的事實,極為明顯。故無論從華南渡來,或由北方經朝鮮半島渡來,日本民族為多元的混成民族,且以大陸系漢人為其骨幹,應為事實。誠如栗山周一氏云,日本人並非日本列島之特產者,亦非自高天原飛來者,乃由大陸大規模之移入。就人類學骨骼研究比較之結果,當時近畿地方日本人骨骼,與其說與近代朝鮮人相似,毋寧說與中國人骨骼的構造完全一致。朝鮮半島的居民,多數為大陸移民的後裔,故日本民族為大陸漢人血統關係淵源很深,中日同種的說法,是有其淵源歷史的根據!
P.25
自大森貝塜發掘以後,一般史學家及考古學家從貝塜遺物之形式種類,把原始時代之日本文化,分為「繩紋式文化」及「彌生式文化」兩種時期。所謂「繩紋式文化」,乃以繩紋式土器為代表之文化。在代表原始日本文化之石器遺跡中,發現有一種黝黑色之土器,其表面有結繩式文字模樣,故一般日本史學家稱之為原日本人,謂之繩紋式文化人。在歷史學上稱為「先史時代」,約距今六、七千年以前,至一、二世紀之間,約當我國周秦之際。在地質學上所謂沖積世之中期,而繩紋式時期,是以漁獵為中心,距離「彌生式文化」之農業社會仍甚遙遠。至西紀前一、二世紀,即繩紋式文化的末期。這時我國已有高度文化,且早於殷商之世,進入農業社會。降及周代更為發達,以前農具皆為木製品,至周代則發明以鐵製造。例如「國語」謂:「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木屬斤,試諸土讓」。所謂美金就是銅,惡金就是銕,農業上之工具,既有所改進,農業生產自當隨之發達。正當我國農業文化發達之時,日本尚處於未開化狀態。當時之日本人,尚過著渾渾噩噩,穴居野處,茹毛飲血之原始狩獵生活之階段。誠如伊東信雄氏所云:「日本在繩紋式文化之社會基礎,係立於狩獵採取經濟之上的氏族制度社會」(註七)。
所謂彌生式文化,乃以彌生式土器為代表之文化。這種土器如同「燒瓦」,帶有赤色,器形比較單純,表面有刷毛式樣之迹象,較之繩紋式土器為具有較高文化之產物。彌生式土器在日本中部以西較多,其
P.26
中尤以近畿中國四國九州方面最多。彌生式文化後期,約當西曆紀元前後,這時期的歷史文化,已稍可從文獻史料上獲得其概況。約當我國秦末漢初。日本於這時期,始產生農耕文化。伊東信雄氏云:「在我國開始農耕;而農耕社會之形成,乃在彌生式時代,農耕文化之發生為人類文化之重大進步,在我國農耕文化之產生,實肇始於彌生式時代」(註八)。但日本彌生式文化,傳自何處?秋澤條二氏亦云:「日本在金石併用時代(彌生土器時代),已盛行農業生產。此一事實,在彌生式土器再發現有籾殼痕,及當時之銅鐸繪畫之模倣等可獲得證明,而銅器及青銅器,在這一時代自中國經由北九州輸入日本」(註九),這說明日本彌生式文化來處。森本六爾氏亦云:「彌生式之文化,乃自大陸渡海而傳入此島(指日本)之文化」(註十)。又說:「彌生式文化,乃藉周末漢初之漢式文化之流傳而飛躍興起之文化(註十一)。由於大陸銅器及青銅器輸入日本,使日本文化發生突然變化,在日本文化發展上大大縮短了歷史上的距離,因為日本只有石器時代,而沒有銅器時代,由於外來文化的影響,使日本從新石器時代,越過銅器時代,一躍而進入鐵器時代。根據晚近於日本九州及大和地方發現有青銅等物考證,證明使日本歷史文化突然發生變化的,是以我國周末漢初文化為母胎,當時大陸移民曾携帶大量青銅器於紀元前後流入日本。據日本梅原末治所著之「由考古學上考察出來之古代日鮮關係」(朝鮮雜誌第百號)中曾說:
「在畿內大和發掘之銅鐸形狀,頗類似先秦時代之古鐘,近年在朝鮮慶尚南道慶州入室里,發現之四寸許小銅鐸及蒲鉾緣細紋鏡,與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在大和國葛城群吐田鄉發掘之遺物,實屬相同。且其製造術均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恐此先行之於辰韓,然後傳至於日本」。
P.27
小林行雄氏亦云:「我國尚停滯於石器使用之低文化階段之際,中國大陸早已經由青銅時代逐漸進入鐵器時代而展開了高度之文明,彼我之間既然一經啟開了通往之道,則如當水性之向低處流,彼地之文物陸續輸入我國,急速地促進了我古代文化之改革,乃不難推察之事。是故彌生式文化,乃經由朝鮮半島而傳日本也」(註十二)。和辻哲郎氏則云:「彌生式文化之出現,若表示異人種渡來,就其文化因帶有秦代銅器之傳統一點而言,此人種不能不視其係來自中國大陸」(註十三)。岡田辛武亦云:「彌生式文化本身,即如大陸系之農耕文化」(註十四)。而美國學者畢拉博士(Dr. Richard K Beardsly)亦認為戰後在唐古、登呂等地發掘所獲之石器及銅器,證明了日本彌生式文化,的確是大陸上中國文化之產物,其傳入日本年代即在公元前三世紀時(註十五)。
中國文化之進步早在殷商時代已燦爛可觀,不但能以銅錫混合冶而作青銅,且能以青銅作成種種器具。降及周末漢初,我國青銅文化已傳入朝鮮,再由朝鮮傳入日本,濱田耕作氏亦云:「當日本石器時代,鄰邦中國於周末漢初之間,已表示出無敵的勢力,向鄰近各地活躍移民,因此,他們所使用之金屬,銅或青銅所造之器物,已隨著傳布東南亞各國,其中一路經由海洲至朝鮮日本。日本接觸中國之金屬,才由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何以知道金屬器是由中國傳來者乎?因為中國古錢刀布,在這一帶都有發現,這是周末的貨幣,可以證明其年代」(註十六)。
在日本所謂「彌生式文化」遺物中,石製的及青銅製的武器,即所謂石刀銅戈,其形式雖不出中國文化範圍,但在年代上確有很大的距離,在多數日本學者所謂「彌生式文化」,是以米為中心的農耕社
P.28
會,(約在紀元前二、三世紀)中國早已進入高度文化階段,此時大陸不僅青銅器早已絕跡,即普通鐵製,已由劔而進化到刀。漢武帝元封三年以後,樂浪郡久成為中國文化散發的中心,何以日本「彌生式文化」與大陸文化之間,竟有此種重大年代距離,迄今仍未獲得結論。同時,在西日本所發現石斧中,多與華中華南所發現相類似,而青銅器中的銅戈,又與先秦時代的戈形式相一致。從這些遺物中可充分看出:中倭於先秦以前已發生往來關係。
王莽貨泉在日本大阪河內郡發現王莽貨泉,這是天鳳一年(西紀一四年)所鑄造的錢幣。南韓慶尚南道的金海貝塜,亦有此種貨幣出土。這種貨幣在大陸上且未多見,而竟在日本出土,更具無比歷史意義與價值。在我國歷史上,這一時期,正是周秦列國,楚漢相爭,最混亂的時期,許多王族在悲歡離散中,集團到處流亡,經朝鮮半島,展轉流入日本,乃屬必然之事。
「明刀」,在日本備後三原町和備前邑久郡山手村,都曾發現過先秦時代的貨幣「明刀」,這種貨幣本自燕國,隨著燕國勢力,分佈於東北和朝鮮沿海一帶,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亦正說明了中國金屬文化傳入日本的路線。
銅劔、銅鉾,在日本北九州及泗國紀伊多有出土,銅劍有三種形式,
P.29
即細型銅劍、平型銅劍、Kris型銅劍。所謂細型銅劍,就是我國先秦時代的「匕首」(見駒井和愛鏡劍玉之研究)。Kris型銅劍,也和我國先秦時代的戈有系統的連絡(貝高橋自日本太古時代中國文化之傳來)。銅鉾可又分為狹鋒鉾與廣鋒鉾,在對馬島、朝鮮慶尚北道、黃海道黑橋驛,以至旅順附近,都見銅劍銅鉾出土(註十七),這說明此種遺物是由中國大陸傳來。
「銅鏡」,在日本畿內筑紫吉備各地古墳中,發現漢式銅鏡極多,銅鐸分佈區域包括山陰山陽北陸畿內東海各地,朝鮮慶尚南道亦有銅鐸出土。梅原末治氏認為銅鐸先發生於古朝鮮辰韓地方,然後傳入的路徑,大概是乘日本海左旋回流之便,先傳至山陰及北陸,漸次傳入內地(見「從考古學上所見之上代日韓關係」)。
這些金屬文化,究竟何時開始輸入日本。據濱田耕作博士云:「從貨泉的發現看來,西日本在王莽時代,即一世紀左右,大體石器時代已經告終,由於漢文化的影響,開始進入金屬時代文化的黎明期,這實在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劃期事件」(註十八)。
我國自秦併天下,以至漢武帝(紀元前一○八年)征服朝鮮半島,先後二百年間,我國文化以後期鐵器文化為主流,分別向東南諸國,浸潤灌輸。然後紀元前一世紀左右,日本始終停滯在新石器時代,但至漢武帝征服朝鮮,設置樂浪等四郡,我國鐵器文化,經樂浪發散各地,由此流入日本,乃為意料中事。因此,日本在極短時間內,越過青銅時代的浪潮,竟後來居上,逐步進入鐵器時代。這已獲得日本多數史學者之公認,已如前述。
P.30
我們從先史學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日本群島原無人類發生,其民族的來源,乃係由外部移入。這種學說,幾為全體考古學家所公認,而成為民族學上之定論。日本民族的祖先必在大陸,日本文化,乃由歸化人所開拓,亦為史家所認定。因此,我們對日本民族的來源,至此可肯定的說來自大陸,大陸民族對日本民族具有充分血統的關係。從前述遺物中看來,日本文化全在中國文化照耀之下,突從石器時代躍進於鐵器時代中,在極短期間之內邁入鐵器時代,更大步走入歷史舞臺,可說全得之於中國文化的庇佑。
朝鮮半島地形,南北狹長,東濱日本海,西臨黃海,南隔海峽與日本相對,這是日本列島與亞洲大陸間唯一的陸橋,在海航未發達以前,中倭遠古時期的交通,多賴古朝鮮為媒介。中國文化,傳播域外,亦以朝鮮為最早。史記微子世家載:「箕子封於朝鮮」,可為證實。當紀元前一一二二年,箕子開國朝鮮。箕子是中國古代殷紂王的叔子,姓子,名胥餘,為太師,封子爵,國在箕,所以人稱箕子。紂王無道,箕子苦諫不聽,周武王伐紂,箕子率封國人民,遠奔塞外遼東,建國朝鮮。故朝鮮歷史文化,雖屬悠久,但開國者,並非朝鮮人,卻是大陸漢人。箕子實為朝鮮文化的始祖,迄今平壤西麓,還有箕子陵,千秋俎豆,中韓兄弟之誼,即奠基於此。
當紀元前二○九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秦朝暴政,燕齊趙民避地朝鮮者數萬人。燕人衞滿率千
P.31
餘人亡命朝鮮,至紀元前一九四年,衞滿襲擊箕準,箕子朝鮮亡。衞滿都王陵(今平壤),與漢約為外臣,服屬鄰近部落。紀元前一○八年,漢武帝元封三年,平定朝鮮,設置樂浪等四郡於朝鮮,衞氏朝鮮亡,是故中韓兄弟之邦,擁有三千三百年文化歷史的關係。
後漢書東夷傳載:「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百濟)是其一國,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
由此可知,三韓方位,都在朝鮮半島南端,是韓國史中的史前部分,高句麗、新羅,百濟,這是韓國歷史的開端。新羅於紀元前五七年,始建國半島南部,韓國歷史由此開始。新羅因受中國南北朝文化影響,這時,由西域傳入之佛教,極為興盛,佛經佛像,競相東傳,於是入華求法,高僧赴韓,相望於道。新羅真興王改皇宮為皇龍寺,剃髮為僧,法號法雲,王妃亦隨之為尼,這時,正當梁武帝捨身同泰寺弘法的時期,高句麗、百濟,都相繼信奉佛教。
秦漢兩代遺民,為避免國內戰亂,相繼逃至朝鮮半島的辰韓地方,故辰韓亦曰秦韓,經辰韓再移居日本九州,這是中日遠古的交通路線。
近世在朝鮮方面,曾經日本考古學者發掘二個出名的貝塜:一是「夢金浦貝塜」,一是「金海貝塜」。這是研究朝鮮半島史前文化主要資料。
「夢金浦貝塜」,在半島中部,黃海道長淵郡南面夢金浦,一九一七年,經鳥居龍藏博士發掘,其
P.32
主要為鐵斧一把,貨泉一枚。金海貝塜在半島中部慶尚南道金海面金峴里,一九二0年,經濱田耕作博士發掘,其主要為布紋陶器破片及石鏃、銛等。在日本也發見貨泉,這是中國前漢末年,王莽篡漢後,所鑄造的貨幣,發行於天鳳元年(紀元前十四年)。這時,中國盛行鐵器,但大陸鐵器能夠傳入半島,必在第一世紀以後,故夢金浦和金海二貝塜構成,當在一、二世紀之間。
在十九世紀初葉,在韓國、日本、琉球,都發見「明刀」古幣,這是中國周秦時代通用的貨幣。在韓國出土的「明刀」多達四千枚,完好的也有二千七百零二枚,每數枚為一束,其底有類似木板物的安置。在日本發現「明刀」有二處,一在備前邑久郡,發現「明刀」和「安陽布」。一在備後御調郡三原町,發現「明刀」,在琉球那覇市外城岳貝塜層中,發現「明刀」一枚。「明刀」使用的年代,據推定約在西紀元前二七三年(周慎靚王四年),到西紀前二二八年(秦始皇十九年)之間。由於韓國發現大量「明刀」,史學家與日本備後前發現「明刀」相結托,不獨認定中、韓、日上代文化交流關係的論證,並定為先秦以前我國民族文化南進,經北韓、南韓移入日本、琉球的鐵證(註十九)。
於此可知紀元前一、二世紀中倭文化交流,經朝鮮半島移入日本的事實,極為明顯。
P.33
日本群島,本無人類發生,其民族來源,係從外部移入,在遠古時代,航海技術尚未發達,外來的民族,是如何渡入日本,這是中倭交通史上必先解答的問題。
據地質學者研究,日本列島在遠古曾與亞洲大陸連接,為亞洲大陸的一部分,距今五十萬年以前,地殼發生激烈變動,有一部分下沉,成為現在的狀態。至於日本列島形成的經過,柯拉曼氏(A. W. Graban)在其所著「中華地層誌」(Stratigraphy of China)一書中,認為在中生時代(Mesozoic),亞洲不僅其東南部與南洋群島及澳洲全島接連在一起,同時中國大陸之東部亦與朝鮮、日本以及菲筆賓各島互相接連在一起。降及新生代(Cenozic)之初期,亞洲之東北部與美洲西北部之連接部分被海流沖斷,而形成白令海峽;亞洲南部與澳洲北部之接續部分,亦逐漸被海流冲斷而形成南洋群島;同時,日本西部與亞洲大陸東部相連部分,亦因地殼之變動陷落而形成日本海,日本列島終於與大陸隔斷,逐漸形成今日之狀態。
日本與大陸被切斷以後,自陷於長期無人島嶼,散列於東海中,其周圍渡至群島,是為以後的事件,這是考古學者所公認,已成為日本民族學上的定論。
據栗山周一氏之「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他說在列島上發掘遺骨及遺物研究,其年代較晚。當原始時代,其周圍民族渡至列島,多以海流為自然航路。今日日本人自稱其民族為大和民族,又稱天孫民
P.34
族或天降民族,謂大和民族之祖先並非自有日本列島以來,即棲居於該島,而是由其他各地移住日本者,此已為今日一般人類學者所公認(註二十)。在原始時代,由外地移居日本列島之各民族,大體均利用海流為其渡日之自然航路。環繞日本列島附近之海流有赤道暖流(黑潮)、日本海海流、千島寒流(親潮)、中國海寒流、黃海暖流、朝鮮東岸暖流(對馬海流)、日本海廻流、以及中國海廻流等。這些海流中,對於古代中國大陸民族之移民日本列島,及中國文化之輸入日本,最有貢獻者為日本廻流路(註二十一)。只以缺乏史籍可徵,以及向來無人調查研究,致為一般人所忽視。直至二十世紀初棄,用投瓶法實地測驗的結果(註二十二),不獨證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經由朝鮮往日本山陰、北陸地方之一種自然航路,並為半島上新羅人多漂至日本出雲地方唯一原因也。日本海流中,原有間宮海峽寒流,與對馬海峽暖流二者,由間宮海峽發源之寒流,沿俄領東海濱省東岸及朝鮮半島東岸南下,適與由南而北之暖流衝突於對馬海峽,因之,其結果溫度低,比重大的寒流,潛伏於溫度高,比重小的暖流之下,並沿其周圍陸地而成為左旋回流。由對馬海流,沿山陰、北陸海岸東北而行,迨至津輕海峽及宗谷海峽,遂分為大小支流,漸次微弱,直至庫頁島西岸而消滅。此種具有左旋實力之日本海流,實為中國民族由半島東渡最古的航路。(以上根據王輯五氏中國日本交通史第一章考證。)
日本海廻流對於古代北方民族之渡海南下移居日本關係最大。例如日俄戰爭之際,俄國曾在海參崴港口外敷設機械水雷,戰後浮流者凡三百十三個,其中被日本海回流漂送到達朝鮮東岸及鬱陵島者有五十個;由日本本州出雲,漂至津輕海峽之海岸及隱歧佐渡者,有一百九十八個,即為明證(註二十三)。和
P.35
田雄亦曾就日本海之環流作一調查,舉出在一千多年前新羅人、高麗人等自朝鮮半島漂著日本之山陰、北陸者有八九十之多(註二十四)。並曾就明治卅九年至大正二年(一九○六—一九一二),日本水產調查會及日本海軍省水路部在朝鮮半島西岸及東北岸一帶海中所投入之空瓶,及明治卅七年至卅八年(一九○四—一九○五)日俄戰爭時,兩國所敷設之機械水雷之漂流日本者加以調查統計,漂著於山陰道者最多,並列一表如下(註二十五):
| 地名 | 水雷 | 空瓶 | 地名 | 水雷 | 空瓶 |
| 山陰道 | 五十一個 | 三十一個 | 北海道 | 四十四個 | 四十五個 |
| 北陸道 | 一百九十七個 | 二百四十三個 | 千島海岸 | 無 | 一個 |
| 東海道 | 十八個 | 一個 | 庫頁島海岸 | 一個 | 二個 |
| 南海道 | 二個 | 一個 | 朝鮮東海 | 六十一個 | 十四個 |
| 西海道 | 一個 | 無 | 琉球海岸 | 無 | 一個 |
以上所引實例,可知古代中國人之赴日者,必由古辰韓地航海抵達日本之山陰北陸地方,再由此轉入內陸。木宮泰彥氏亦云:「只因日本海回流路,為自然的航海路,且開闢甚早,故大陸民族,由此航路漸次移住於日本各島。此時中國文化亦經由此航路波及於日本」(註二十六)。王輯五氏亦云:「綜觀在
P.36
秦以前,由中國渡海涉倭國者,則往往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自朝鮮半島向日本之山陰地方漂著,這可由銅鐸之遺跡分佈狀態獲得證明,此誠為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東渡之最古經路」(註二十七)。由於朝鮮南部與日本畿內所發掘的銅鐸,不獨彼此相同,其製法與形態,都顯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朝鮮慶尚南道的新羅國及辰韓之故地,當常趁日本海左旋回流漂至日本山陰地方。由兩地發掘銅鐸,均相一致,足以證明海回流,當為中國民族文化東渡最古之航路。
秦代以前中倭間之往來航路,雖缺乏現代資料可資印證,但秦始皇時徐福之渡海赴日本,記錄於史記,足可徵信。徐福入海東渡日本前後共有兩次(或三次):第一次當為秦始皇二八年,第二次當為秦始皇三十七年(註二十八)。第一次渡海之路線,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十年條之記述,其航路地點當為自琅邪,經由方丈(濟州島),而瀛州(琉球群島),最後至蓬萊島(日本)。第二次渡海赴日本之航路,我國史籍及日本史籍,均無痕跡可尋;據衞挺生教授之研究,當係由徐州揚州一帶海港,直捷經由濟州島附近而至九州之博多灣(註二十九)。據衞挺生教授之研究,徐福渡海之赴日本,前後共三次。上述徐福第二次赴日本,則與衞挺生教授研究之第二次相同。因第一次乃少數人之探險,到達九州西北部之宗像海岸登陸,僅作一簡短之地理考察,由此次考察之結果,而決計前往殖民,遂假借仙人靈藥之說賺秦始皇,予之童男女數千人,資之五穀種籽,與百業之技工及工具;始皇允令徵發,遂徵人物及船第二次入海。由琅邪出港,沿東海南下,循中國海回流路經沖繩島、瀛洲(琉球群島),最後達到蓬萊島九州,至日向登陸。近世在球琉那覇市外岳地下出土的「明刀」幣,可能是徐福一行人中的遺物。唐
P.37
代日本遣唐使所取道之南島路,即由筑紫大津浦出發後,經平戶島、屋久島,經沖繩島南航,橫度中國東海,直達長江口,故知中國海回流對於漢族移住日本關係極大。(詳第三章各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