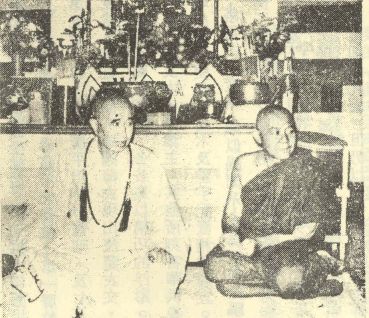余於一九七一年秋,就印度及印尼兩地敎友邀請,前往訪問。於訪問印度回程,經曼谷至星加坡,初下榻天竺寺,後至菩提閣。由羅浩然先生陪同前往印尼,十一月四日抵達雅加達,是日體正法師率領諸多善男信女至機場迎接,當日下榻太平洋漆廠,次日移錫廣化寺,訪問市區各道場。並於同善堂午餐,於雅加達佛敎會歡迎會講演「孔子關公都在印尼」,聽衆全係信佛的華僑,講詞如次:
『丘會長、諸位居士,今天我能在此與諸位會聚一堂,首先要感謝三寶加被!這次我是從印度朝聖回程,經過曼谷,星加坡來至印尼。昨日訪問雅加達市區各寺院,及諸位敎友,看見各寺院莊嚴建築,清淨道場;又見到許多善男信女湧到寺院燒香,焚燒紙錢,那種傳統風俗,完全與祖國一樣。實是令人有不知身在異域之感。同時,我又聽說,印尼政府禁止華文敎育,及華文圖書進口,但信仰佛敎的僑胞們,仍在暗中研讀華文的經典,所以在印尼唯有在寺廟裏才能看到華文圖書,那麼寺廟不啻為保存中國文化的褓姆。因此,我覺得諸位在此不僅盡了弘揚佛法的責任,也盡了保存祖國文化及民族傳統的義務。
同時,我看見許多寺院裏,不獨供奉了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並發現孔子與關公,都成為佛敎的貴賓,儒釋一家的精神却出現在印尼。並且佛殿兩邊墙壁又繪畫了岳飛、文天祥,許多忠孝節義民族
P.312
的故事,這對旅居海外僑胞來說,實寓有一種民族敎育的意義。這使我回想到三百年以前,創建寺院的高僧及善信的一番用心。印尼各地寺院,大都在明末清初時興建。當時正是滿清入關,明朝垂危的時期,鄭成功據守臺灣、福建,誓志恢復大明江山失敗後,許多忠貞愛國的志士,不顧做滿清的順民,為情勢所迫不得已捨離祖國的懷抱,不是東渡日本,就是南移星馬、印尼。許多來到印尼的志士,以身在海外,只有藉著佛敎來掩護,所以他們興建寺院,用意很深。不獨要供奉佛像,宣傳佛法,並且要供奉孔子、關公。也就是假寺院弘揚祖國文化,藉關公的忠義來團結民族的志士,仍圖有所作為。這種莊敬自強的民族精神,值得我們每一中華兒女學習與記取。明末清初南移同胞的處境,正與你們今日在海外同胞處境相同。因此,我要奉告諸位,你們雖在海外,但每個人不特與中華七億五千萬同胞有血緣的關係,並與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同一根源。所以我們不僅要宣傳佛法,並要弘揚祖國文化,始不負當年移植祖國宗敎文化於海外的忠貞志士的一番苦心。要知當年南來的明末遺民,都是諸位的先遠宗親,他們之所以南移,絕不是為了保存自己有限的生命,離開祖國,實是為了保存祖國五千年歷史文化道統,及民族的氣節,才來到海外定居。今日我們宣傳佛法,弘揚祖國文化,也就是發揚當年南移忠貞愛國的祖先精神。
丘會長昨天告訴我印尼佛敎會發展情況,現有七十多所分會,有會員二萬多人,居士會有一萬多人。雅加達有會員六百多人,印尼全國佛敎徒約一千萬人以上,這是一個有系統組織的團體,也是發展印尼佛敎基本的力量。同時,七十多所分會,多半為印尼人所領導,這顯出中印一家的象徵。根據一九二
P.313
九年北京周口店所發現的北京人,與一九三六年泗水所發現的爪哇人,經專家研究的結果,北京人與爪哇人為同族遠祖。因此可以說中國人與印尼人為同一民族的血統,印尼國民來領導弘揚佛法宣傳中國文化,可說最為適當。佛敎對於印尼歷史文化有過輝煌的貢獻,他們應當記取發揚光大,使印尼成為亞洲七十年代最優秀的文化,最進步的民族。
今日人類世界彼此不能合作,就是互相猜疑與仇恨。唯有宣揚佛敎慈悲的思想,消除人類的仇恨,世界始有和平的希望。
今日因時間關係,不能與諸位多講。好在隨後講話的機會,還多得很。』
蘇門答臘與爪哇,同為印尼兩大主要大島,又同處在西部,當東西交通的要道,所以最先接受印度文化,而與我們往來也最早。印尼古代政治文化的建樹,首先成立國家,也是在這兩島上;而印尼佛敎歷史的重心,則在蘇門答臘,不在爪哇。
蘇門答臘,簡稱蘇島,或曰室利佛逝,或曰末羅瑜、或曰三佛齊、或曰舊港,都屬同一地的異稱,因其產金,故又稱金洲。
十世紀以前,則有蘇門答臘、室利佛逝、末羅瑜、金洲諸稱。十世紀起,迄於明初,則有三佛齊;夷屬爪哇後,又改稱舊港。十五世紀以還,只有舊港名稱。
P.314
蘇門答臘建國,約在七世紀時。建都於渤林邦(Palenban)城。統治此國的山帝(Cailendna)王朝,統有蘇門答臘全島。當七世紀半頃,即六八六年,因闍婆(爪哇),不願稱臣,便發兵征服了闍婆;但其統治闍婆的時期,至九世紀後半葉,即告終止。至十三世紀末二十五年間,因兩次遠征錫蘭失敗後,又被爪哇征服,並易其地曰舊港。蘇門答臘古代帝國,遂土崩瓦解,降為爪哇的保護國。
七世紀時蘇門答臘,不獨宗敎文化為南海的中心,且為中國、印度海上交通第一站。我國取道南海前往印度求法高僧,十之八九皆取道蘇門答臘,其取道爪哇者較少。就中以運期、彼岸、玄逵、善行、大津、貞固、懷業、金剛智、義淨等最為著名。
一、運期,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仗智賢(即爪哇中部人若那跋陀羅)受具(即從智賢學崑崙語)旋回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言。頗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約在六九二年。義淨經其地時,此人尚在,年約四十餘歲(求法傳上)。
所謂崑崙語,即古爪哇語,名迦維(Kawi),七世紀時蘇門答臘,即今之渤林邦(Palenban)都操此種語言。大津、貞因、懷業等都解崑崙語。
二、彼岸法師、智岸法師者,都為高昌人。……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策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並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留室利佛逝國矣(求法傳上)。
三、玄逵傳云……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約在六七一年),漸學聲明(Cabda vidyā)。所謂聲明,就是梵文文法。於六七二年,舉帆漸向東天矣。及其歸程並將梵本三藏(Tnipitaka)五
P.315
十餘萬頌,唐譯可成千卷,擁居佛逝矣。
四、義淨……義淨西行,始於六七一年,終於六九五年,凡三至室利佛逝。第一次在六七二年,留佛逝六月。留學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梵本經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唐譯可成千卷。第二次於六八五年經印度而至佛逝,留住四年。因缺少紙筆,乃寄書廣州,求得紙筆,在佛逝從事譯經工作,並請得助手多人。在六八九年,因商人順風,舉帆高張,在無意中被載至廣州,竟將梵本經論遺置佛逝,乃於當年冬天復偕貞固等四人重返佛逝。因得貞固等協助,從事譯經工作。第三次在六八九年以後,留時亦久。前記之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二書,乃撰於六八九至六九一年之間。寄歸傳曰:「末羅遊(一作瑜)洲,即今蘇門答臘是。又據義淨所述,七世紀下半葉,其地文化甚高。淨初蒞此,經停六月,漸學聲明。又謂佛逝不止千僧,勤學好施,亦如中土(中印度),軌儀相同。漢僧西行求法者,應先於此持戒二年,然後再往中天。可見室利佛逝之梵學、佛法,皆為義淨所推重。而其地之古馬來語,亦為義淨、運期、大津等之所閑習矣。(見蘇門答臘古國考九六頁),因此,義淨停留蘇門答臘至少在十年以上。」
五、僧法邁,於九八三年,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Vimalacni)願至中國譯經。一○○三年對宋上書,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為額,併以鐘賜焉。其頃服於宋室可知矣。
由此可知七世紀時,蘇門答臘,不僅梵學佛法興盛,「不止千僧」。彼岸、智弘、玄逵三人,既將
P.316
大乘經論傳至蘇門答臘,當時其佛法必屬大乘敎無疑,其國勢強大,不獨征服闍婆(爪哇),而近佔馬來半島,遠服柬埔寨,其聲威之大,更可知矣。
爪哇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關係,雖不及蘇門答臘,但亦有其重要的立場。在六朝時代,印尼是中國與印度海上交通重要的門戶,也是佛敎從印度傳入中國的轉運站。六朝時期,我國高僧經印尼前往印度求法者,雖多取道蘇門答臘,但取道爪哇者亦復不少(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而最早到達爪哇者,則為西晉法顯法師。法顯於三九九年,由長安出發,橫渡亞洲大陸,訪問印度八大聖地,在外十五年,於錫蘭求得彌沙塞律藏本、長阿含、雜阿含,以及一部雜藏,都為當時中國所缺少者。經錫蘭乘船東歸,經九十日航行,乃到一國,名耶婆提(爪哇),「其國婆羅門敎興盛,佛法不足言」。因當時爪哇既沒有佛法,於是法顯便成傳佛法於爪哇的第一人。法顯停留爪哇五個月,然後携彌沙塞律藏本、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回到中國;於是爪哇成為印度佛敎傳入中國的轉運站,這是四一四年事。
法顯停留耶婆提五個月,弘傳佛法已成定論。法顯後十年,東來之求那跋摩(Gunavarman);初至闍婆(爪哇)弘化,當時爪哇國王備加敬禮,國王的母親並從其受戒。未幾又飭國王受戒,後來國王對佛法發生熱烈的信仰,乃發心欲出家修道,經羣臣勸止,國王乃對羣臣約法三章:
P.317
一、凡王所統領國土一律尊奉「和尚」為師。
二、統治境內一律禁止殺生。
三、國家所有儲蓄財物,散賑貧病,羣臣歡喜敬諾,於是終止出家,舉國皆從其受戒。國王又為跋摩建立精舍,導化之聲,遠播遐邇。四二四年,宋文帝乃遣使至爪哇,請跋摩來建康,四三一年,跋摩始來廣州。
由此觀之,四二四年跋摩所至之闍婆,則道化大行,若為爪哇。則四一四年法顯所至之耶婆提,「佛法不足言」則必非爪哇,應為蘇門答臘,二人所至必為二島。七世紀義淨所見室利佛逝之興盛,則五世紀亦當富強也。
七世紀中,經爪哇前往印度的我國高僧中,而與印尼佛敎關係最密切者,則以常愍、明遠、曇潤、會寧最為顯著。就中以會寧,最為傑出。
會寧,益州成都人,於六六四年至六六五年間,由海道至訶陵州(爪哇),停住三年,遂與印尼高僧若那跋陀羅(Jnaabhadra,爪哇中部人),從阿笈摩(Agama)經內譯出湼槃經後分二卷。大乘湼槃經,總數有二十五千頌,譯成可達六十餘卷,會寧與若那跋陀羅合譯後分,僅得二卷,乃命運期寄達交州(宋高僧傳卷二)。印尼高僧與中國會寧合譯經典,這是中印佛敎史上最有價值的記錄。
由此觀之,印尼佛敎,不論蘇門答臘或是爪哇,其與中國佛敎歷史關係至為密切。要依傳承而論,應以法顯為始,次為求那跋摩。以此類推,則為若那跋陀羅、會寧、大津、義淨、貞固、法朗、道宏、
P.318
孟懷業。因此,印尼佛敎,不僅與中國佛敎高僧法顯等有密切關係,即中國佛敎部分經典,實從印尼傳入,於是印尼便成為中國佛敎經典輸入地區之一。而中國佛敎諸多大乘經典,經彼岸、智弘、玄逵等傳入印尼,使印尼佛敎與中國佛敎發生更為密切關係。蘇門答臘,在歷史上雖有這許多輝煌的記錄,但荷蘭統治印尼時期,以爪哇為根據地,以巴塔維亞(Batavia)為首都。因此蘇門答臘,遠不足與爪哇相比。同時又缺少文物的依據,更不及爪哇尚保有九世紀半夏連特拉王朝(Sailendna)所建的闍婆佛塔,頗有考古價值。據近人許克誠先生「荷屬東印度古代略史考」載:唯爪哇之有佛敎,當由於印度移民於其地建立王國所致。印度人在爪哇所建王國之馬達蘭姆(Matanam),自西元九二五年後,已日漸衰亡,而為東爪哇之回敎王國所代興。故佛樓與佛像之創建,最晚亦當在西元九二五年以前,即五代後唐同光二年以前。近人於佛樓臺基下曾發現簡單銘文,謂西元八五○年左右,即唐宣宗大中四年左右所建立。而另據近人於荷屬蘇門答臘所發之碑刻考之,則爪哇阿的亞哈瑪大王(Maha-Rajaudinajaaditiy adharma)於西元六五六年,即唐高宗顯慶元年,曾於爪哇建造七級浮圖,說者即此佛樓(見唐代文化史研究一○七頁)。但諸多說法,仍以九世紀半建立最為有力(參見本章第六節)。印尼最古的石刻,據雅加達博物館所藏的石刻佛像,則為八世紀及八世紀中葉;因之,闍婆佛塔當為九世紀前後所建,殆可確定。今日欲考證八世紀以前印尼佛敎歷史,則非藉重中國佛敎傳記及梵文、波斯文,以及東西名人史地考證筆錄不可;否則,無法尋找印尼佛敎史上有價值的根據。
十三世紀回敎興起,印尼佛敎日漸衰微,十五世紀後,便入長期睡眠狀態中。
P.319
余於一九七一年訪問印尼,對印尼佛敎曾作進一步考察。印尼佛敎,原屬南傳小乘佛敎,因彼岸、智弘、玄逵等將大乘經典傳入印尼。所以今日印尼佛敎,既非小乘敎,亦非純大乘敎,乃大小混合的佛教。但華僑所信奉仍屬大乘敎,雖不及十世紀時興盛,但印尼佛敎仍有着光明的前景。自蘇哈托總統接掌政權後,佛敎在各宗敎平等的原則下獲得自由發展。印尼政府所承認的五大宗敎,則為回敎、天主、基督、佛敎、孔敎;各個宗敎都可自由發展,佛敎也就獲得了復興的機會。由蘇拉濟准所領導的印尼佛敎會,刻有七十多所分會,正式會員貳萬多人。蘇曼德利上校所領導的居士會,則有會員壹萬多人。各省市佛敎分會,多為印尼人領導。華僑固多信佛,但印尼人信佛的亦復很多。現在印尼佛敎信徒,至少在一千萬以上,這是印尼佛敎有系統組織的機構,也是復興印尼佛敎基本的羣衆。印尼佛敎寺廟,約三百多所,分布在全印尼境內,僅蘇門答臘,就有七十多所寺院,雅加達大小有三十多所,以廣化寺、金德院、南華寺為最大;住衆以靜福堂、同善堂、祥慶堂為最多,也最清凈。現在比丘十四人,比丘尼五位,沙彌尼五位,次為出家未剃髮者,約一百多人。印尼政府雖承認孔敎,但印尼並沒有正式的孔廟,唯佛敎寺院,多供奉孔子及關公的聖像,並在佛殿墙壁,或走廊內繪畫了歷代忠貞愛國的故事,這對旅居印尼的僑胞來說,實寓有一種民族敎育的意義。這使我們回想到三百年以前,興建寺廟高僧的一番用心。印尼的佛寺,大都在明末清初興建。當時正是滿州人入關,明朝垂危的時期,鄭成功據守臺灣、
P.320
福建,企圖恢復大明江山失敗後,許多忠貞愛國的志士,不是東渡日本,就是南移星馬、印尼。所以旅居印尼的僑胞,多為福建人,次為客家人,再次為廣府及潮州人。印尼華僑,至少已有三百年至四百年歷史,在華僑人口中,福建人居半數,多數居爪哇,婆羅洲西部多客家人,蘇門答臘東部及邦加、及勿里洞諸島,多潮州人。外地各島的人數,比較在爪哇者多。現在全印尼華僑至少有五百萬人,保留中國籍者,僅三十多萬人。當日南來印尼的明末遺民,以身在海外,只有藉着佛敎來掩護。所以他們興建寺廟,不獨要供奉佛像,並要供奉孔子,以及關公;甚至要繪畫忠貞愛國的故事,來啟發民族的志氣。也就是要假寺院來弘揚祖國文化,藉關公的忠義精神,來團結民族的志士,這種忠貞愛國的精神,雖未達到他們恢復大明江山的目的,却達到他們保存祖國文化的目的。這種莊敬自強的民族精神,值得我們每一中華兒女學習與記取!同樣的,印尼佛敎寺院,雖未積極推行佛敎文化,却在消極方面盡了保存祖國文化的責任。
中國與印尼之關係,早在二世紀初雖有接解觸,但僅屬國際上聯絡,談不上文化關係。五世紀初,法顯抵達爪哇,携回彌沙塞律藏、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停留爪哇五個月,弘揚佛法,此為印尼佛敎的基礎。
十五世紀,是世界航海史上建立功業時代,歌倫布於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加馬於一四九八年發現
P.321
印度新航線。麥哲倫於一五二○年發現南美洲及菲律賓。這幾位都被公認為世界「航海偉人」。可是中國的鄭和從一四○五年起,就開始率領一百多艘大船,二三萬隨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了七次,走徧了印度洋沿岸地方,先後共二十多年,到過三十幾個國家,我在三寶壟參觀「三寶洞」,以及雅加達公園裹的鄭和予土人的四尊礮,這些輝煌的記錄,使我更加領悟鄭和的偉大;不特世界航海偉人不能與鄭和相比,而鄭和所表現的中國的人力,財力和卓越的智慧,更是世界史上無堪比擬的。誠如張君勱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為三寶洞所撰對聯曰:
這是最確當的寫照,刻仍懸掛在中爪哇三寶洞門前。
中國是以王道文化為主,鄭和七次下西洋,所表現天下為公,信義和平的精神,是西方文化所沒有。當時中國雖擁有龐大艦隊,絕不用侵略,或征服的手段來對付各個弱小民族,各個國家,完全用建立信義和平的方法,達成和平相處,天下為公的目的。所以中國在東南亞沒有一寸的殖民的領土,這是王道文化的精神。假使鄭和肯用少許的船隊,採取征服主義,不僅可扼守麻六甲,並且不待一五一一年、及一五九年,葡萄牙人、荷蘭人佔領麻六甲,而荷蘭人更不能到達印尼,則中國早已佔領了整個東南亞。並可遠拒日後英法荷艦隊於印度洋之外,則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地,都不至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不僅如此,則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以及百年來一切喪權辱國的戰爭,都不致發生
P.322
,則中國近代史必大大改觀。甚至不獨為亞洲一大海權國家,且為世界一大海權強國。由於中國王道文化重義輕利的精神,以及融和萬邦的政策,所以鄭和七次下西洋。都以傳播中國王道文化,對南洋各島嶼的人民,都以打抱不平的態度,及除暴安良的手腕,保護各島人民安居樂業。在明洪武年間(一三六四至一三九八),有廣東陳祖義逃避於此,率衆橫覇,剽掠過客,至永樂間(一四○三至一四二四)經三寶大人擒捕正法,始告太平,就是一明確的答案。因此,迄今南洋各島,各國人民無不懷念鄭和愛民的恩澤,於是麻六甲有三寶山、三寶廟,中爪哇有三寶洞、和三寶井,都是為懷念鄭和而設的紀念。中爪哇的三寶洞,不特香火很勝,而印尼政府對三寶洞名勝,也特別保護。至三寶洞燒香感恩的人,不僅為華僑,也有印尼人在內。相反的,荷蘭人統治印尼三百多年,印尼全境却沒有一塊紀念荷蘭人的碑文,這就是東方王道文化勝於西方覇道文化的證據。
我在印尼時間,雖不太多,由雅加達至三寶壟,循公路前往,沿途經茂物、萬隆觀光所見印尼山明水秀、土壤肥沃、物產豐富,可謂「天府之區」。並參觀印尼最著名的闍婆佛塔。對印尼佛敎歷史以及東西各島地形作一鳥瞰式的觀察,並參觀三寶洞,使我發現王道文化精神的可貴。原想至巴列島,及蘇門答臘作進一步考察,因時間限制未能前往,只有留待他日。體正法師要我寫一部「印尼佛敎史」;因為印尼佛敎歷史文獻不太多,只有從各地寺塔古蹟、碑記等詳加考察,採取資料,則非逐島踏查搜索不可。
P.323
這一工作,對我來說却是一件有意義的任務,能否完成,只待時機因緣來決定。我對闍婆佛塔,也作了一次考證。
近世印尼及巴列島發現有關密敎梵文寫本佛像,多屬密敎性質。足見印尼嘗奉行過密敎,這是屬於大乘佛敎的一種。現在爪哇島從Buro-Budui起自Jabang, prambanarm, Melang, Panatarang, 及Tumpng,都有莊嚴寺塔存在。就中Buro-Budur中部Kadu縣Magerang佛塔,最具考古價值。西曆一千八百十四年,英國總督Rattles始發掘,即介紹於世界。這是印尼現存佛蹟中最偉大者。但許多小塔內所安置的轉法輪釋迦牟尼佛坐像,僅是一尊無頭佛身,以及諸多部位遭受有計劃的損毀,其受毀的理由,或說由火山爆發、或回敎徒所毀。但其建造雄壯,僅塔基見方四百二十一尺,共為九層,最頂上為一大塔,總高約二百尺,用暗黃色岩石砌成。從基層至第五層,取複几帳面,第六層取單几帳面,均為方形。以上七八九三層為圓壇。而第七層上三十二座小塔,第八層壇上二十四座小塔,第九層壇上中央大塔外,別有十六座小塔。合計七十座同型同大的小塔,相輪為八角柱,所作輪等。此等塔皆立
P.324
於大蓮臺上。各塔中央安置轉法輪契印結跏趺坐釋迦佛像,塔身周圍,各穿六十四個菱形孔。第九層中央所築大塔,是本建築的中心。基底直徑五十三尺,露盤上有高大八角柱相輪,今上半已損毀。各層連接的階段,四方為同一型式;各層貫通中央,一直線達第九層。第一層至第六層其型狀逐漸縮減,其餘副部充露天廻郎;其間兩側壁面,無餘寸地,彫刻佛傳及本生譚等圖相。就中內壁分上下二段,上段多數設佛龕,內安置坐佛像。用尖拱,橢圓拱等為印度式。並施以微細裝飾文樣,又龕頂上安小塔形,層層重疊佛龕林立,佛龕所安佛像,第一層第二層的廻廊各百四尊,第三層八十八尊,第四層七十二尊,第五層六尊,第六層平坦不作龕形,及七八九三層小塔內合七十二座,凡五百四尊。其造像手法多為印度式,相好圓滿,透過薄衣現出流麗衣文,彫法妙極。又龕背面上層外側壁及內壁下段壁面分上下二帶,更縱區劃數額面,各各施以精巧的浮彫。額面總數二千百四十餘面,其中千七百餘面,今尚完全,畫面以佛傳及本生譚為主。其他所刻香華供養及風俗等多種,其構想極為巧妙,全副能維持緊張,羣像姿勢頗富有變化,樹木及屋宇配置相當適宜。充份顯出豐滿雅麗的風格。柱為健馱羅系,亦有屬中印度系;塔為中印度系,類似錫蘭系,或為緬甸先驅。其他細部的手法等,而與中國、安南、柬埔寨等系同工異曲的例子亦復不少。其採用各國樣式手法,可說為集多種樣式混合而成。其建築年代亦有多種說法,近人於佛臺基下曾發現簡銘文,謂西元八五○年左右所建,另據近人於蘇門答臘所發現之碑刻考,則為爪哇阿的亞哈瑪大王(MahaRajud-inajanditiyadhanma)所建。其於西元六五六年,於爪哇建造七級浮圖,說者即指此塔。但仍以九世紀半頃所建最為有力。
P.325
現在Prambambanarn, Buro-Budur東南二十里地方。有七個佛寺存在。就中Chandi Lolo Jongrang建築為最古,劃七百二十尺四方為外圍,內建百五六字小堂,又內圍劃二百六十尺四方,內建六字堂,如是小羣堂,構成一佛寺,其他與此類同型。
印尼屬於熱帶地區,其本國有關歷史文獻存在不多。佛塔,却為考證印尼佛敎歷史文主要的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