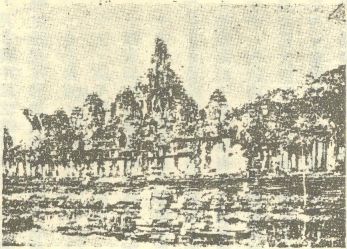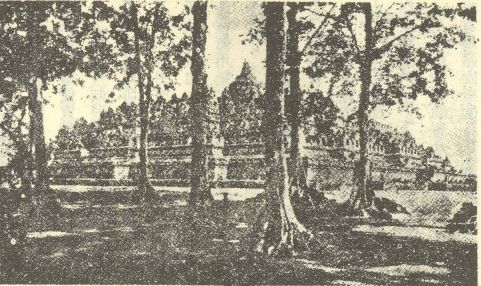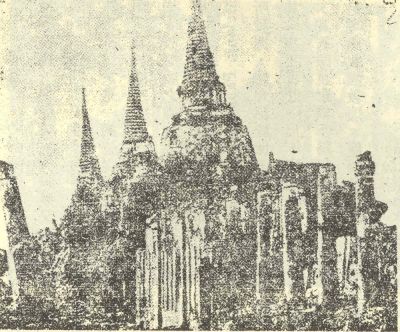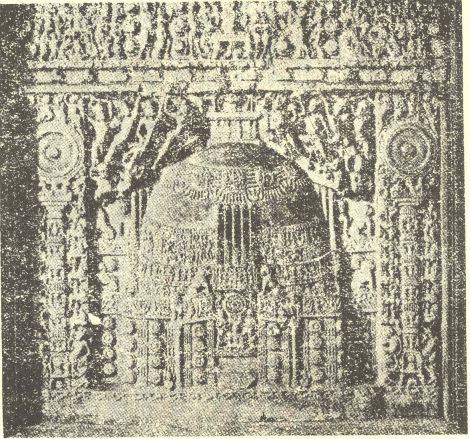魏晉南北朝時,西域交通大衰。魏時「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但西域不能盡至。晉時武帝泰始中及太康中僅康居、焉耆、龜茲、大宛、大秦來貢。北朝時西域交通,幾全中斷。故宋、齊、梁、陳,皆以海道與印度交通。唯北齊與西域,僅有信使往來,得覊縻勿絕之道。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
茲據正史中有關與南海諸國往來記述,擇錄於次:
三國志卷三十,對印度之記載,有浮屠誕生,漢哀帝元壽元年景盧受浮屠經等。並記有車離國及盤越國,似即漢西域傳之東離國及盤起國。記盤起國曰:「盤起國一名漢越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此與張騫紀元前出使大夏時見有蜀布筇杖,尋諸市曰,從身毒國來,其經過事實大致相同,可知中印間商賈早有交通也。
晉書苻堅傳上,記晉孝武太元六年(三八一)天竺國獻火浣布於苻堅,梁書及南史則皆記晉安帝義熙初(四○五)師子國來獻玉像,師子國即今之錫蘭島。印度商人僧伽剌Singhala冒險經商於島上,並建國為王。師子國為僧伽之譯音,可知其時中印間已有海上交通,我國高僧法顯於四一三年從錫蘭乘
P.286
商舶而返國者。
宋元嘉五年(四二八),師子國王剎利摩訶奉表曰:謹向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為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詳後節)。此所謂道人,乃指佛敎沙門而言,「白衣」,乃指在家信佛者,均未列名。可知當時中印間政治使節往來記錄,而遺漏者頗多。
梁書海南諸國傳總敘曰: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故不載官史。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
北史有婆利傳,謂自交州,海南過赤土、丹丹而至其國,似即婆羅洲。天監十六年(五一七)來獻金席,普通三年(五二二),又獻方物數十種。
丹丹國,見同上,似即今馬來吉蘭丹地,大通二年(五三○)遣使奉表,奉牙像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吉貝、離香藥等。大同元年(五三五),又遣使獻金銀、瑠璃、寶香、藥物等。南海又有賴遜國,見萬震「南州異物志」。及康泰「吳時外國傳」。梁書諸夷傳稱其與扶南、交州、天竺、安息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寶貨物,無所不有。梁書五十四記師子國,蓋採自佛國記,梁時
P.287
師子國遣使奏表,其中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等語,其內容與大宋明主奏表,大致相同,當時中印間使節往還,雖屬政治成分居多,然在師子國的目的,則在共弘正法。佛敎於紀元前三世紀中葉,即阿育王時,傳入師子洲,殆為南傳佛敎中心。而緬甸、柬埔寨之佛敎。同屬此一系統。
所謂南海,其範圍極廣,蓋包括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以西,以及印度羣島。元朝以前,此一地區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但正史中有關南海諸國著錄,僅有宋書夷蠻傳、南齊書蠻夷傳、梁書諸夷傳,各書所記頗多參差。李延壽所作南史夷貊傳,乃總其成,而列為十五國。計為
| 一、 | 林邑國,即今占婆(Campa),安南中圻。 |
| 二、 | 扶南國,即今柬埔寨。 |
| 三、 | 訶羅陁國。 |
| 四、 | 呵羅單國,在蘇門答臘島。 |
| 五、 | 婆皇國,即Pahan,今在馬來半島。 |
| 六、 | 婆達國。 |
| 七、 | 闍婆達國,宋書作「闍婆婆達」,或誤闍婆與婆達為二。 |
| 八、 | 盤盤國,似在馬來半島。 |
| 九、 | 丹丹國。 |
| 十、 | 干陁利國,在蘇門答臘島。 |
| 十一、 | 狼牙修國,今之Lenkasuka,在馬來半島。 |
| 十二、 | 婆利國,今爪吐東之Bali島。 |
| 十三、 | 中天竺國,在今印度。 |
| 十四、 | 天竺迦毗黎國,在今印度。 |
| 十五、 | 師子國,即今錫蘭島。 |
以上所舉,殆為南海諸國中主要者,其中與中國有政治往來者,僅數國而已,其餘均為納貢。而與佛敎關係較密者,則為扶南、林邑、闍婆、蘇門答臘、師子國等。
中國與南海諸國交通,應上溯至紀元初,南方交州已為中國所征服,中國與交趾支那半島之各民族相接。大秦王安敦之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末中國雖分三國,吳帝孫權曾遣康泰朱應出使扶南。當康泰朱應二人未至扶南以前,扶南王已遣人使天竺,謁茂論王。
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國條曰:吳時(二二二至二五八)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
P.289
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㫋,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其王號茂論(按茂論王即印度古籍中之 Mouroundas,其建都於曲女城,即古之Kanyakoubdja今之Kanauj。關於此事之考證,法人 Sylvain Lévy著有未詳之二種民族Deux puples一文,刋於méconnus Mélanges de Harlez集中,見沙碗中國之旅行家)。又赤烏六年(二四三)十二月,扶南王范㫋遣使獻藥及方物。據此則康泰朱應之出使,乃於范㫋後王范尋在位之時,始達扶南,於此可知扶南早與印度有交通也。
晉書曰:「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
扶南或跋南,印度支那半島南部國名,即今之柬埔寨,王及大臣皆號為崑崙。古之賴遜,似即今之 Tenassenim,扶南之一屬國也。國王名崑崙,馬來半島之盤盤,或為古代柬埔寨之一屬國,大臣名崑崙。馬端臨曰: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之古龍者。但扶南與中國發生關係,始於漢武帝時(紀元前一四○至八六年),印度洋諸國皆至中國朝貢。當時之交趾,已列入中國版圖,漢末亂時,交趾曾為避亂之所,而又為西亞與東亞交易輻輳之地。一六六年羅馬安敦之使,即於此地登陸,因之使中國與交州至東羅馬通道中發生關係。自林邑(今安南東岸)以西,在紀元初數世紀,其任務最大者,莫過扶南也。據圖書集成引吳曆曰:黃武四年(二二五),扶南等外國流離,此流離即 Prakrit 文之 Verulya,梵
P.290
文之 Vaidurya,即玻璃也,此玻璃必非扶南土產,似由印度輸入也。扶南(吉蔑)與林邑(占波)雖與中國毗鄰,但因言語隔閡,受中國文化之影響不易。後漢書謂:「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頂髮徒跂,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當孫權遺康泰朱應使扶南,從事宣化,當時扶南人尚無衣服,赤體露胸,唯婦人著貫頭,吳使見之指責,扶南王范尋遂傳令國中男女,為尊重中國使臣,皆穿橫幅干幔(即紗籠Sarong),由是扶南人始有裳服。第四世紀末葉,扶南王亦有名憍陳如者,乃印度人,神語曰,應為扶南王。憍陳如至,盤盤扶南人迎立為王。遂改變風俗,厲行天竺制度,敎民習印梵之學,鑿井取水,與製造塑像等工藝。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隋代遣使貢獻,唐武德後,亦頻來獻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至洛陽,由此觀之,扶南國從三國時代始漸擴張國勢,至初唐時始繁榮,相次入唐朝貢。於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於此發生接觸,同時,於此構成中印文化分水嶺,故有印度支那之稱呼。今之柬埔寨為印度化,交趾支那為中國化,是有其歷史的因素存在。
據梁書海南諸國傳第四十八:憍陳如於天監二年獻梁朝珊瑚佛像,同十八年天竺獻㫋檀瑞像娑羅樹
P.291
葉等。又大同五年武帝聞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乃遣沙門寶雲迎接。
扶南與中國佛敎關係,據續高僧傳卷一,扶南國僧人,名僧伽婆羅,生於四○六年,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梁天監五年(五○六),武帝敕召於扶南館、壽光殿、及正觀寺占雲館等五處傳譯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一部四十八卷,歷經十有七年。普通五年(五二四年)卒,年六十有五。
又歷代三寶記第十一:梁天監初,有扶南沙門名曼陀羅,五○二年大齎梵本,遠來楊都,勅與該國僧伽婆羅共譯寶雲經等三部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
梁大同(五三五)中,勅張氾送扶南使返國,仍請求名德三藏,及大乘諸論雜華經等,彼國乃屈請真諦三藏並齎經論,於五四六年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轉來南京。其附傳有彼國僧須菩提於楊都至敬寺,為陳主譯出大乘寶雲經記載。於此記載當時該國主要為大乘佛敎,亦有解脫道論Visuddbi-magga流通。據沙碗考證佛馱跋陀羅從南海經扶南而至中國(見亞淵報一九○○十二月刋)。
明史真臘傳第二百十二:隋唐及宋皆來朝貢,宋慶元中,滅占波並其地,因改國名曰占臘,元時仍稱真臘。明洪武三年以來屢來朝貢。萬曆以後改號柬埔寨,當時即為暹羅所破,後又遭安南侵入,十八世紀時為暹羅及安南屬國。一八八四年起為法保護國,二次大戰後,始獲獨立。
由以上所舉觀之,康泰等所立記傳,今可考者,朱應有扶南異物志、唐書藝文志,並著錄,今佚。但康泰等之足跡,似未過滿剌加海峽,或曾附扶南船,歷遊南海諸國,絕未至印度,此可斷言也。當康泰未赴扶南之前,扶南既有使赴印度,復觀其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及「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可
P.292
證知印度文化早有流入,故扶南之印度化,當在紀元之前,似無可疑。但至三世紀初葉經康泰等宣化,扶南國民始有裳服,此為受中國文化宣染之影響。五世紀初僧伽婆羅來華譯經,以及大乘論師真諦三藏,來自扶南,其受佛化尤深,故扶南實為中印文化交流地區,迄今柬埔寨仍遵守印度佛敎制度,而與緬甸、泰國同屬小乘上座部系。其所書寫經典,稱為巴利文三藏,其與錫蘭殆屬同一語系。交趾支那,則遵守中國佛敎制度,其九世紀初闍邪跋摩Jayavarmany Angkon Thom,(現今Tonlé-sap湖以上約十四里處)為都,興築宮殿伽藍及佛窟,自此經十數代繼續施工,至十二世紀始完成其工程,此項佛窟,迄今仍存在。此與爪哇Bolo-Budur佛窟,同為東南亞最大之佛窟。而與中國北方敦煌、龍門石窟,遙相呼應,同屬亞洲著名之佛窟也。
隋煬帝纂業,頗懷大志。遠求異珍,討伐高麗,出師流求(今臺灣),加兵林邑(安南中圻),通使倭國,南撫赤土,西達波斯。踐祚雖暫,國威殊隆,而開闢南海交通,企與漢武帝開闢西域,發揮神武,先後輝映。其有關於南海交通之開闢,則為常駿等出使赤土國。
大業三年(六○七),帝賜常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遺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
所謂赤土,隋書卷八二赤土傳曰:赤土國,扶南之別稱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
P.293
「常駿等發自廣州,沿安南海岸行,過Camao峽,入暹羅灣,沿真臘緬甸海岸行(因有島嶼連接之故),至馬來半島北部東岸,望見狼牙須國之山。南行過馬來半島東岸之一島,而名之曰雞籠島,然後抵於赤土國界。則此赤土應在馬來半島之中」。此據中國南洋交通史所載,其說「狼牙須」,即梁書之「狼牙修」,續僧傳之「棱伽修」,南海寄歸傳之「郎迦戌」。
今考常駿等行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今之廣州)乘舟晝夜二旬,而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Lingaparvata),西與林邑(今安南中圻)相對,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西望見狼牙修國之山。
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界。駿以六年(六一○)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據費瑯考訂,「常駿發航之廣州,航經林邑,沿真臘之南岸,至Camau角(在安
P.294
南南圻之北柳)。西渡暹羅海灣,至馬來半島東岸之Ligor地方偏南之海岸。沿岸北行,此處亦島嶼,然不及通考所誌之多。旅經「狼牙修」,此地即Lenkasuka,在南緯七度四十三分。雞籠島為南緯十度之一島,赤土國應在Kra地峽以北,暹羅灣西岸之一地也。此對常駿行程之解說,而予文考定之根據,則以狼牙修即Lenkasuka為起點(見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馮承鈞之「中國南洋交通史」謂,則以赤土應在馬來半島之中,舊書謂在暹羅境內誤也。
由以上所引各節觀之,中國與南海諸國交通,紀元前二世紀,漢使足跡,雖曾達南印度境,然僅限於貿易及朝貢,對國際文化傳播,毫無關係。三國時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今之柬埔寨),隋代常駿等使赤土,亦僅沿安南、真臘、馬來半島,並未遠至印度,且亦越過滿剌加海峽,故對文化上並無重大之影響。
中國史籍記錄,中國至印度,或由印度至中國之海上行程,最正確之記錄,則首推法顯之佛國記,法顯於四一四年自師子洲附舟至耶婆提(Yavadvipa)。質言之,即自錫蘭逕赴爪哇(闍婆),十數年後之求那跋摩(Gunavarman),歸時亦遵此路。
爪哇國(Java),在中國史籍中有葉調、闍婆婆達、訶陵、耶婆提、爪哇諸名,是皆指蘇門答臘,殆為爪哇古稱之同名異譯。此外太平御覽卷七八九有諸薄,或杜薄。宋書首著闍婆婆達。闍婆乃其對音,
P.295
婆達蓋衍文也,高僧傳卷二則作闍婆。唐書中闍婆作訶陵,降至元代,島夷志略始有新譯名曰爪哇。爪哇與中國發生關係,早在二世紀初,後漢書南蠻西夷列傳云:「永建六年(一三二年初),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此中葉調即闍婆之舊音。
於此可知一三二年既遣使至中國朝貢,其王名調便,調便即梵文Devavarman之譯音,可知當時爪哇必早與印度交通,而受印度文化已久。此調便Devavarman名為一種尊號,其義猶言天祐,國王既用此外來之尊號,不僅可知一三二年時,此島早受印度文化之熏染,而對其必發生熱烈之信仰,始用此尊號也。又現今爪哇的言語有awj Knam二種,就中後者乃從梵語發源而來—其文字又同於印度半島常使用梵字Deuo-nagaj;其他,此國火山等名亦不少冠以梵名,這些,足以證明受印度文化影響很深。
當印度最初傳布文化至爪哇之時,其人民之程度必與越南半島馬來羣島及馬達伽斯伽(Madagasacr)島之野人相等。據費瑯說,馬達伽斯伽島土人說:『相傳彼等祖先,在二千年前,由海外之一地移此。』此海外地方,應為馬來羣島,爪哇人印度化之前,其程度或不及馬達伽斯伽島之土人,馬達伽斯伽土人,尚能憶及其祖先來自海外一地,而爪哇則鮮有憶及其祖先來自恒河東方者也。十三世紀阿拉伯著作家賽德(Ibnsa''id)謂,馬達伽斯伽島已為馬來羣島人移居之地。據阿拉伯作家耶德力西(Edrisi)說,「馬達伽斯伽島人為爪哇移民,彼此通曉語言」。蓋非洲以東之語言,能歸入馬來羣島西部語言者,唯有馬達伽斯伽島語言而已。十二世紀之爪哇語與馬達伽斯伽語,必較今日兩地語言尤為接近。由此推
P.296
想馬來羣島語輸入此島之時,必在十世紀之前,此據費瑯考證。
據後漢書所載,一三二年時爪哇王名調便(Varman)同一尊號,印度數王朝之君主已曾用之,而爪哇調便之遣使至中國,必早知海外有一強大中國,故入貢以求保護。此種外交政策之運用,非具有高尚文化,熟習國際政情者,不克為之。故爪哇受印度文化之渲染,可溯至紀元以前,蓋一種文化之輸入,必須經過長時間之化育,始能發生作用,故恒河以東各地(南海諸國)之印度化,必亦在紀元以前也。
法顯於四一四年,自印度回國,「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法顯曾留耶婆提五月,耶婆提Yavadvipa經伯希和考訂為爪哇,已成定論。近人有誤其為美洲,純出於臆斷,毫無史實之根據也(詳別章)。
高僧傳第三求那跋摩,其於法顯後十七年,來至建業。其本罽賓王種,早歲出家,深究律品,妙入禪要。至年三
P.297
十,不就王位,乃辭師違衆,遁迹人世。後赴獅子國,觀風弘敎,遂至闍婆(爪哇)弘化。王母婆多加特加敬禮,從受五戒。未幾又勅王受戒。後王敬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經羣臣諫止,王乃就羣臣請三願: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禁止殺生,三願所有儲蓄財物,散賑貧病,羣臣歡喜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又為跋摩建立精舍,導化之聲,遠播遐邇,四二四年宋文帝遣使請其來華,乃於四三一年,始來廣州。四一四年法顯至耶婆提時,「佛法不足言」,至跋摩抵其國後,舉國歸崇,故闍婆之佛法,至五世紀初,由跋摩開化,始見發達,義淨所記南海十洲中訶陵洲,即為闍婆,唯根本有部,故當時爪哇佛法純小乘敎也。現今此島從Euno-Budun始至Jabang, Pnambanam, Kediei, Melang, Panatanang及Tumpang等,仍存有偉大寺塔。西曆一千八百十四年,為英國總督S,Kaffles所發掘,始介紹於世,為南海中現存佛蹟中最著名者。其破壞之原因,不外為火山及回敎徒所摧殘也。其塔基四百廿一尺,築九層壇形,其頂上作大塔,總高有二百尺。各層外浮彫佛傳及本生譚,內供聖像,其造像及彫刻多為印度式、健馱羅式,為錫蘭、緬甸佛塔之先驅。其築於九世紀半,其彫刻之手法,足可以與我國敦煌、龍門及安南、柬埔寨之佛窟相媲美。
義淨之赴印度,其往返皆取海道,其行程記錄,最為可信。六七一年,發自廣州,順東北信風,南行至佛誓(Palemban),海行十五日,至蘇門答臘東岸Jambi河上之末羅瑜(Malayu);又十五日,
P.298
至馬來半島西岸之羯荼(Kedah);從羯荼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Iles Nicohar)。向西北行半月餘,抵印度Hoogly河上之耽摩立底(Tamralipti)。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無行傳,謂與智弘為伴,東風汎舶自交州一月到室利佛逝國(Palemban),行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又西行經三十日,到印度東岸之那伽鉢亶那(Nagapattana);又二日,到獅子洲(Ceylan)。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貞固傳云:「淨於佛逝江口升舶,附書凴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經,並雇手直。於時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求往無路,是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元年(六八九)七月二十日達於廣州。……所將三藏五十餘萬頌,並在佛逝,終須復往。……誰能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有僧貞固……斯為善伴,廣府法俗,悉贈資糧,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而長驅」。
六八五年,義淨自耽摩立底歸中國,路經羯荼、佛
P.299
逝,留佛逝四年,於六八九年至廣州。同年又偕貞固至佛逝。後於六九五年仲夏始還至洛,則其最後居佛逝時為年亦久,合計其往來南海之時間,應有十餘年。
七一七年,金剛智自獅子國赴廣州,行一月至佛逝。又據宋高僧傳金剛智傳云:次復遊獅子國,東行佛逝、裸人等二十有餘國。
又大津傳,乃齎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年,解崑崙語,頗學梵書。
室利佛逝(Sriboja),此為梵名或名佛逝,亦名佛誓,或名佛齊,或三佛齊,並作尸利佛逝(Palemban,關於此種種名稱,可參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及冊府元龜諸文)。即蘇門答臘(Sumatra)東南,即原書之巴林馮,亦作浡淋邦(Palemban),舊港。此島為印度文化東漸之第一站。而室利佛逝國地處東西交通之要衝,故梵文、大食文亦有著錄,大食人名此國曰:Jawaka, zabag. Sribuza,此國文化雖古,然與中國交通,僅盛於唐、宋、元、明,四朝。唐代求法高僧取道南海者,多寄舶於此。義淨之求法高僧傳有尸利佛逝及佛逝種種名稱記錄,續高僧傳金剛智傳中,有佛誓及佛逝;新唐書所誌六九五年及七二四年朝貢,作尸利佛誓,九○四年朝貢,此國名佛齊。自此以後,中國史籍於此一地名,則目之為佛齊,或三佛齊。
以上所舉,法顯及求那跋摩之行程,直接自錫蘭島至選他(Sonde)峽,金剛智則經Nicobar島,滿剌加峽至佛逝,復由此至中國。義淨行程則為廣州、佛誓、末羅瑜、羯茶、裸人國、耽摩立底。當時之佛逝,或室利佛逝,亦即今日之Palemban,蓋為佛敎高僧西行所必經,或由斯地迎接佛敎大德東
P.300
來,多遵此路。由此觀之,無論中國高僧西行,或印度高僧東來,乃至西方商賈,皆取道滿剌加海峽而停室利佛逝也。故自七世紀以還,中印間之航路,過滿剌加峽(Malaka),及馬來半島之東南沿岸,斯為中國遊記之航路也。至阿拉伯人則取道滿剌加峽,及星加坡峽。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註云:「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窮盡,有大黑山(Arakan教),計當吐蕃(Tibet)南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羅(Sniksetra)國。次東南有郎迦戌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Campa)國,並悉極遵三寳。」義淨之郎迦戌國,應是狼牙須之同名異譯,而位在室利察呾羅國之東南。此室利察呾羅國,即唐書中之驃國。驃即今之緬甸,唐以前亦曾以剽國名緬甸也。社和鉢底國即Menan下流之Dvaravati,臨邑即林邑之別寫,即今安南中圻也。
同書卷一記南海諸洲云:「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又云:「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洲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
義淨所記諸洲,最西之洲,為婆魯斯洲,其為今日之Baros無疑也;此港以輸出樟腦著名,其在
P.301
蘇門答臘之西岸。次為末羅遊洲,在Jambi河流域,莫訶信洲,亦即太平寰宇記之摩訶新,此國即十一世紀與當時爪哇王Er-Langa戰爭之Mabasin。現未考定其地,唯據義淨所記,則在尸利佛逝之東,應為爪哇西部之一獨立國也。訶陵洲似為爪哇之中部或東部,訶陵次之,為呾呾洲。唐會要記此國在訶陵之前。呾呾洲、盆盆洲,疑在馬來半島。婆利洲應是Bali,隋書卷八十二云:「婆利國(Bali)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則此國在東京婆利之間也,新唐書卷二二二下云:「單單國在振州(海南島)東南,多羅磨之西。」多羅磨今雖未能考定其地,然據義淨所記之次第,此地應為爪哇海之東部之一嶼。盆盆洲,應即西域求法高僧傳中之渤盆,在訶陵(爪哇)之北,似為今之Madura島,蓋其次第在婆利(Bali)之前,祇能位置於此也。
掘倫洲,在訶陵之東方,即今日地圖上之Goram島,地處Geram島之東南。次為佛逝補羅洲,經高楠順次郎考定其元音為Bujaypura者也,今爪哇島之東Remban南府中,有一行政區,名Bojanegara,音與佛逝補羅相近,姑誌於此,以備考定。
阿善洲之原音,應為Ajan或Ejan及Aja或Eja,然今未能知其為何地也。
末迦漫洲,其古音為Markaman或Markaban。爪哇古詩經第二十五詩有一Markkaman,克洛每(Krom),考定其地在Pasuruan之南,以上十洲地名之考證,皆據費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紀元前一二世紀,中國使節雖曾達到南印度,然未至師子洲。玄奘周遊五印度,對師子洲雖有著錄
P.302
(請參閱大慈恩傳卷五),但亦未至師子洲。義淨往返,均由南海至東印度南界之耽摩立底國着陸,亦未至師子洲。我國高僧中最早至師子洲者,唯法顯耳。法顯於三九九年循陸路前往至南印度海口多摩梨帝國,停留二年,寫經及畫像,便乘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即今錫蘭島。留住二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長、雜阿含,及雜藏一部,此為中土所無者。復乘商人大舶,得好信風,經九十日許,到昔耶婆提,即今之爪哇也,法顯於四一四年青州登陸。四二九年有外國船主難提土量曾載師子國之比丘尼來建業;及元嘉十年(公元四三三),難提再來中國時,復載來師子國之比丘尼鐵薩羅等十一人(見比丘尼傳)。法顯歸後百年,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均為中印度人,經師子洲而東來中土。至唐代中國西行求法高僧,若明遠、窺沖、慧琰、大乘燈、僧哲、無行等,皆曾先後至師子國,禮拜聖跡。
金剛智、不空為傳密藏經典至中國者,金剛智南印度人,曾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泛海東行,經佛逝等二十餘國,開元七年(七一九)至廣州,開元二十年卒於洛陽。其弟子不空,北印度人,奉其遺命,復往五天及師子國,求取密典;天寶元年(七四二)由南海前往,經訶陵而達師子國。天寶五年(七四六)還京,大歷九年(七七四)卒,春秋七十。此二高僧為中土密敎之始祖,其對密敎貢獻殊大。
中國史籍有關錫蘭記載,法顯及玄奘傳記之譯文,歐洲漢學家無不研究。烈維曾將中國與錫蘭之關係作一全部研討(見一九○○年五月刋亞洲報)。三世紀康泰使扶南時,或已知有錫蘭,扶南土俗,現存殘文中,固未見其名;然有斯調洲,似為Sihadipa, Simhadvipa, 譯寫之對立,可參照太平御覽卷七八
P.303
七,但其方位,又似不相符。至五世紀初年,法顯傳始著錄師子國之名,此名沿用至於近代。五世紀下半葉竺芝扶南記,又譯其音作私訶條,相類之譯名,並見於佛經譯文之中,或作私訶疊,亦作私訶絜。十二遊行經所言南海諸洲中之斯黎,疑亦指錫蘭,大藏中屢見之寳渚(Ratnadvipa)亦其別名。玄奘名此島曰僧伽羅,義淨名曰僧訶羅,皆指今之錫蘭。今名古譯,首先諸蕃志曰細蘭,此為最古之譯名(請參閱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
正史中宋書始有傳,其與中國政治上關係,蓋亦始於斯時。宋書卷九十七師子國傳曰:
師子國,元嘉五年(四二八),國王剎利摩訶南奉表曰:「謹向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為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十二年(四三五)又復遣使奉獻。
梁書五十四師子國傳曰:師子國天竺旁國也。……
晉義熙(四○五至四一八)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大通元年(五二七)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向大梁明主,…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勅,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新唐書卷二二下師子國傳曰:「師子國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寳,以寶置洲上。……總章三年(六七○)遣使者來朝,天寶(七四二至七五五)初,王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
P.304
、寶瓔、象齒、白氎。」
從以上引證,可知晉、梁、唐時,中國與錫蘭關係往來甚為密切。並欲與中國共弘佛法,其尊重中國文化於此益見。至明朝鄭和下西洋,中錫的關係,曾發生極不愉快之事。事雖由錫蘭引起,自此中錫關係日漸冷落。據明史卷三二六錫蘭山傳曰:
永樂中(一四○三至一四二四),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鄰境,屢邀刼往來使臣,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廷,羣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並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宣德五年(一四三○),鄭和撫諭其國。八年(一四三三)王以遣使來貢,一四三六至一四五九,先後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
由此觀之,錫蘭為南海中之大國,其地廣人稠,物產豐富,僅次於爪哇。為中印海上交通終點之一,但中國西行求法高僧,咸以印度為目的地,錫蘭僅為經過而已。以錫蘭所傳為初五百年小乘敎,中國乃承受印度之大乘敎,故大乘論師若玄奘、義淨,均未至其境,僅列其名耳。
崑崙為中國地理書中有名之大山,山在中亞。相傳為紀元前十世紀時,周穆王見王母處,自是以後,崑崙之名遂散見各書。義淨所記之掘倫洲,究指何地?據義淨之解釋:「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
P.305
喚崑崙國焉。」但史籍中以崑崙為名者不祇一地,似為捲髮黑身人之總稱。茲據各史籍傳記引證於次:
(一)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一之解釋曰:「崑崙語,上音昆、下音論,時俗語便亦作骨論,南海州島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馴伏猛獸犀象等,種類數般,即有僧祇(Zangi)、突彌、骨堂、閤蔑(Khmer)等,皆鄙賤人也。國無禮義,抄刼為活,愛啖食人,如羅剎惡鬼之類也,言語不正,異於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
(二)太平御覽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在林邑西千餘里,自立為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為崑崙。』
(三)舊唐書卷一九七林邑傳云:「自林邑以南,捲髮黑身,通號崑崙。」
(四)續高僧傳卷二彥琮傳(五五七至六一○年間),『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筴,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舘,付琮披覽』。
(五)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運期傳:『師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依智賢(即訶陵人若那跋陀羅)受具。旋回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
(六)義淨所記南海中奉佛法者,有掘倫島。義淨曰: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高楠順次郎考訂崑崙,即在今之Poulacondore島,其英譯之義淨南海寄歸傳序云:『其島有漏壼,有佛經有丁香。』
(七)大津傳曰:『永淳二年(六八三年),振錫南海……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
P.306
崙語,頗習梵語。』
(八)貞固傳曰:『又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業……至佛逝國,解骨崙語。』
(九)宋高僧傳慧日傳云:「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獅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
(十)金剛智歿於七三二年,遺命其弟子不空赴天竺。據宋高僧傳不空傳曰:『影堂既成,追諡已畢,曾奉遺旨,往五天竺并師子國。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既達獅子國,國王尸羅迷伽迎之。』
(十一)唐僧鑑真,赴日本傳布戒律之始祖也,其弟子Aomino Matto Genkai,撰有行紀,據鑑真所說…七四九年時,廣州珠江之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船舶無數。」
(十二)日本天皇延鑑真至其國,「隨行人有崑崙人一人,名軍法力。」
(十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崑崙諸國,閤蔑為大。』
(十四)據通典卷一八八扶南條云:「隋時(五八九至六一八)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崑崙之訛。」根據此種記載,則崑崙國即國王大臣以古龍或崑崙為國名,顧崑崙為習見之名稱,與其說崑崙訛為古龍,無寧說古龍訛為崑崙也。扶南即今柬埔寨,現柬埔寨有省名曰「崑崙」,今尚存為柬埔寨及暹羅國王之Krun也。一六七三年入貢中國之暹羅王號中尚有古龍二字,暹羅昔為柬埔寨之屬地,故崑崙與柬埔寨關係較為密切也。
P.307
至於崑崙語及崑崙國之由來,迄今仍曖昧不明。但彥琮傳曰:「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筴,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義淨曾屢言中國沙門在室利佛逝國,習崑崙語;慧琳在一切經音義引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謂閤蔑為崑崙諸國中之大國,敬信三寳。舊唐書曰: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為崑崙,準是以觀,似越南半島南部及諸國之人,大致皆名崑崙。義淨所言室利佛逝國之崑崙語。曾與梵語分別言之,則祇能為馬來語或爪哇語。五百六十四筴崑崙語佛經之數,至足驚人。從前占波經文,似無如此之多,馬來文學比較晚,僅有爪哇似有不少撰述。然不能將古爪哇語Kawi之撰述上溯至隋代。或者續僧傳將崑崙語與梵語混而為一,不能謂非異事。總之此書為吾人現有知識所不能解決之問題也(請參閱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六五頁)。
據以上引證,則昔日崑崙國乃泛指南海諸國,北至占城,南至爪哇,西至馬來半島,東至婆羅洲一帶,甚至遠達非洲東岸,皆屬崑崙之地也。
我國與南海諸國交通往來之記錄,應溯至紀元前(一四○至八六年),漢武帝時,印度洋諸國皆朝貢中國,二四五至二五○年間,當時我國與印度、占波、扶南、爪哇、馬來羣島等國,不僅有國際交往,並有貿易、文化的交流。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五世紀初起法顯及求那跋摩,由錫蘭島至巽他(Sonde)峽,六○六年常駿使赤土國,六○五年時,隋伐占城,此就顯著者而言。金剛智則經Nicoarb島、滿剌
P.308
加峽至佛逝,復由此至中國;義淨則由廣州、佛逝、末羅瑜、羯荼、裸人國,而達東印度海口耽摩立底着陸,轉赴中印度。隋唐時經南海赴印度之高僧多達四十餘人,對我國海外航線提供最珍貴之經驗,更有助海外華僑之發展。當時之佛誓,或室利佛逝,亦即今日之Palemban,蓋為佛敎僧徒路程所必經,或因斯地為中印文化傳播地區,因此佛敎高僧,多遵由此路程。總之七世紀以還,中國、印度間之航路,過滿剌加峽(麻六甲),及馬來半島之東南沿岸,此為中國高僧赴印之航路也。
我國之有南海,猶如英法之有地中海。自臺灣至Billiton島,西唯有滿剌加海峽可通,南僅有Banka及Karimato二峽可涉。此外自蘇門答臘至福建,皆島嶼陸地相接,其東南及南方,為波羅(Bornéo)島及菲律賓羣島(Philippines)所限,呂宋(Lucon)與臺灣之間,及臺灣與福建之間,有寬數百里之海道通東海,此即昔日阿拉伯水手所稱之「中國門戶」也。
我國與南海諸國交通,初則限於國際交往,以及僧徒住返印度經過其間。但政治上往來,三國時代,先有康泰朱應使扶南;隋代常駿使赤土。軍事上行動,先有隋伐占城(六○五年),元朝忽必烈可汗遠征爪哇,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以及遠征錫蘭。這些皆可證明國人對遠洋航業具有豐富經驗,並有充分海軍的力量,可以運用。但可惜的,國人未能把握天賦的機運,以中國當時航業而論,其船隻已能到達大海中,並有甚盛貿易,未能發現美洲猶可,而我國航海家何以未能發展到澳洲,乃至菲律賓?而望之於四世紀末,法顯隻身自錫蘭經南海飄至青州登陸,以及七世紀義淨往返印度皆取道南海能無愧乎?沙門冒險與勇敢,所表顯民族之精神,無遜於張博望與班定遠也!而六世紀時中國人已知製造火藥,其
P.309
用煤及煤氣生熱,更早於歐洲者,凡數百年。又何以不能發揮其豐富經驗及智慧,利用商船及海軍固守「中國門戶」。十六世紀以後,國人果能固守滿剌加海峽,則南海必名符其實成為中國內湖,這不僅可遠拒英法艦隊於印度洋以外,則星加坡、馬來亞、菲律賓不致淪為英美殖民地。果爾,則鴉片戰爭、中日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以及百年中國一切喪權辱國的戰爭,都不致發生,則中國近代史必大大改觀,不獨為亞洲一大海權國家,且為世界一大海權強國矣!由於國人僅重視大陸忽視海洋,以致未能固守「中國門戶」,不僅喪失南海諸國,而中國沿海,百年來受盡了西方帝國主義海盜威脅與侵略。乃至今日固守臺灣,究其遠因,實由於海權與大陸未能同時并重所致也。今後欲保障陸權,必須海、空、陸三權並重。
P.310